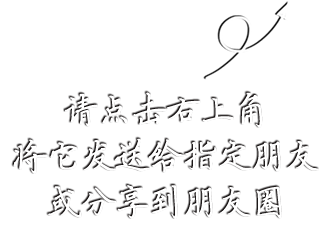□陈博涵(重庆)
父亲帽檐上的警徽,是一枚划分晨昏的界碑,将他与我们寻常人家的烟火日常悄然隔开。三百六十五个日夜,一百天在值班室的灯火里熬成霜白,一百天在异乡的风尘中步履匆匆,余下的时光,也常被突发的警情撕成碎片,化作映亮归途的零落星光。童年里,日历上那些我用红笔圈出的归期,多少次在空荡的餐桌旁悄然褪色,像一枚枚沉入夜海的落日,无声诉说着等待的漫长。
父亲爱工作,他为工作尽职尽责,每天不仅要接警、出警、打击违法犯罪和为民做好事,而且还要处理许多危险的突发事件呢!他平时工作很认真,还经常加班加到很晚,工作上的事情他也想得很周到,所以他经常受到别人的称赞。也因为工作很少回家,对我的陪伴很少,哪怕是在周末,也有加班的时候,让他抽不出时间陪伴我。
然而,父亲的爱,从未因这长久的缺席而稀薄。它只是沉潜下来,烙印进另一种更深的年轮——那是他身躯上,一枚枚无声诉说的亲情勋章。
一个夏夜,我看见他臂上那道新愈的刀痕,如同蜿蜒的暗红色溪流,在灯光下静静流淌。“追个小毛贼,蹭了下,没事,结案了。”他轻描淡写,仿佛在谈论天气。可当我指尖小心翼翼触碰到那微凸的印记,他肌肉瞬间的紧绷,泄露了未曾言说的惊险。那一刻,我指尖下的温热仿佛灼烧着心房——原来英雄的史诗,是以血肉为纸、忠诚为墨,一笔一划镌刻而成的。我终于懂得,他每一次转身离去的背影,都是在无声中将身躯铸成盾牌,稳稳立在危险与我之间,这份沉甸甸的守护,是亲情最坚硬的铠甲。
深冬时节,他脚踝上顽固的冻疮又如约而至,深紫色的硬块盘踞在皮肤上,是雪夜漫长蹲守时,刺骨严寒刻下的勋章。眼神扫过那些粗粝的冻痕,泪水毫无预兆地滴落——原来超人并无金刚之躯,我的英雄,只是以凡胎肉体,在冰霜荆棘中为我踏出一条平安归途。这伤痕里的痛楚与坚持,是亲情无声的负重前行。
晨光熹微中,父亲再次整装。我轻轻环抱住他挺直的脊梁,那里没有披风猎猎,却自有千钧之力,撑起一片苍穹。最深的亲情,是穿透缺席的表象,读懂那沉默背影里全部的守护,于无声处听惊雷——他双肩所承载的,何止一个小家的檐下温暖?那枚闪亮的警徽之下,是广袤人间的岁月静好,无声诉说着一位父亲,以热血与忠诚写就的、最辽阔深沉的亲情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