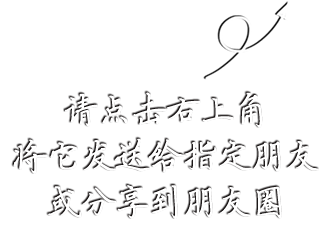□杨福成(山东)
讨厌喧嚣。
喜欢喧嚣。
不知道什么是喧嚣。
这几种对待喧嚣之间的态度,看似有一定的逻辑,实则又没有一点逻辑。
这几种对待喧嚣之间的态度,看似是一种人生的成熟,实则又是一种并不成熟的表现。
说这也好,说那也罢,都不会影响的事实是,喧嚣始终活跃在我们身边,活跃在我们心内。
在我工作室的窗外,有一片工地。
白日里,那动静是粗糙而蛮横的:打桩机像一头患了心绞痛的钢铁巨兽,沉闷地、一下下捶打着大地的胸膛;钢筋与水泥的撞击,是冷兵器时代两军对垒的碎响;工人们偶尔的呼喝,则像钝刀划过粗粝的砂纸。这声响是有形体的,有重量的,甚至带着温度和尘土的气味。你嫌它聒噪,它便愈发地理直气壮,不容分说地填满每一寸空气的缝隙。这是“可听的喧嚣”,你至少知道敌人来自何方,大可以关上窗,用一层玻璃给自己造一个脆弱的结界,或者,在心里暗暗地骂上几句,也算一种宣泄。
然而入了夜,工事停了,另一种喧嚣便浮了上来。
那是寂静的喧嚣。
先是一种极细微的、却又无所不在的“嗡”的底噪,仿佛这城市在轻微地耳鸣。而后,远处高架上永不停歇的车流,化作一阵阵潮汐般的叹息;空调外机单调的呼吸,起起伏伏;不知哪家未关严的电视,漏出几丝含混的、鬼魅似的笑语。
这时的喧嚣,失了白日的形体,变成一种弥漫的、氤氲的氛围。它不刺耳,却更缠人。它从窗缝里渗进来,从墙壁的毛细孔里渗进来,甚至从你自己的血液里泛上来。
你无处可躲。
这时你才发觉,白日的“闹”是一种霸道的宣告,而夜的“静”却是一张温柔的、无所不包的网。
前者是拳脚,后者是内息。
这倒让我想起《世说新语》里的王子猷。
他住在空宅子里,便令家人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他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
这个小故事向来被解作风雅,可我总觉得,那深夜对竹的啸咏里,未尝没有几分对抗寂静之喧嚣的悍然。
竹叶的飒飒,是他为自己生命调定的、属于自然的频率。他用一种清响,去平衡、去覆盖那无边的、空洞的静。
古人没有机器的轰鸣,但他们有更深的寂静,那寂静里,藏着宇宙洪荒的耳鸣,藏着生命本身的喧哗与骚动。
王子的竹,便是他精神的工地,一种主动的、优雅的“造响”。
如此说来,喧嚣大约也是分“体面”与“不体面”的。
机器的噪音,算是不体面的喧嚣,粗暴直接,目的昭然。而“风声、雨声、读书声”,则成了体面的喧嚣,因其有自然的韵律或人文的寄托,便被我们的心安理得地收纳,甚至吟咏。
我们用后者来抵御、或者说,来粉饰前者。我们津津乐道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却绝口不提,若真将他老人家窗外的牛车马嘶换成今日的柴油引擎与喇叭,那“心远地自偏”的功夫,怕是要更上十重楼阁方能修得。
古罗马诗人卢克莱修说:“站在岸上看船在怒涛中颠簸,或是立在悬崖边静观战场上的搏斗,会生出一种“崇高的快感。”
或许,当我们自身暂免于那最直接的喧嚣,而能将其置于一定的距离外“观瞧”时,那噪音便也成了风景,那骚动里,竟也能品咂出一丝关乎存在的、冷峻的哲理滋味来。
细想,白日“可听的喧嚣”与夜晚“寂静的喧嚣”这双重的喧嚣,又怎么不是这时代粗重的呼吸与纤细的颤音?
在这无休止的声浪里,最终,我们都还是要回归到那古老而新鲜,被我们称之为“生活”本身的寂静。

寂静与喧嚣
作者:杨福成(山东) 时间:2025-12-31 次数:334
CopyRight 2009-2022 © All Rights Reserved.版权所有:新渝报 未经授权禁止复制或建立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