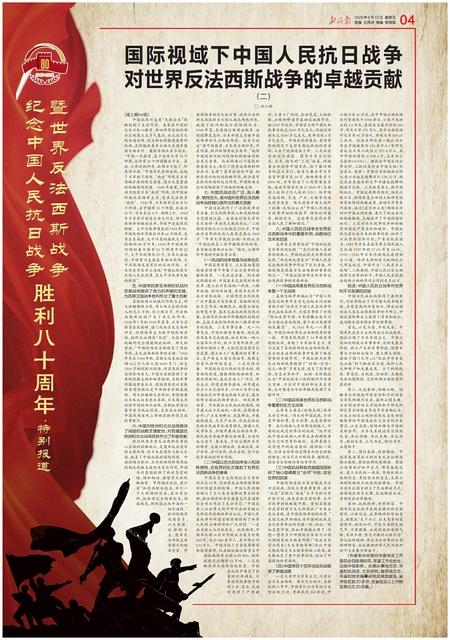A8:渝周刊·龙水湖
□邹安超(重庆)
1937年,抗战爆发,国民政府搬离南京,移迁重庆。
随之,重庆便受到侵略者的狂轰烂炸,而此时重庆却是个几乎不设防的城市,防御能力差,没有任何对空的装备,日军飞机在天上易于来去自如,导致大量房屋被毁,死难同胞数以万计。
一座炸弹随时都可能在身边炸响,死难时常陪伴左右的城市,人们生活如无根的浮萍,四处飘荡。面临灾难,陪都重庆无所惧怕,有一股暗流,在市民心间,在重庆的每一幢残垣断壁里,坚定而执着地滋长。
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去!——似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指引着,给人希望,给人力量。
由此,同胞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对侵略者的谴责和抨击,作为画家的傅抱石,更是拿起手中的笔,如鲁迅先生那样,以笔为武,以墨为诛,创作出反映抗战精神的旷世画作《巴山夜雨》。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巴山夜雨》画作如炬力量再次袭入脑海,便有了谈谈此画作的艺术生命与时代意义的冲动。
首先,《巴山夜雨》是动荡时代的艺术映射,抗战语境下的精神抗争
1939年,为了生计谋职于国民革命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傅抱石先生,是年4月全家避居重庆,落户歌乐山金刚坡下赖家桥附近。
这里属乡下,傅抱石一家租住在一户地主原来的杂物间里,居所阴暗,狭小,既无客厅,也无书房。作为学者和艺术家的傅抱石先生,贫穷和不安定的生存环境,要修身研学,非常不易,但他却著书立说,谈生活,谈艺术,还积极撰写时政言论。
1943年,依旧是金刚坡的农舍,矮屋淅沥、连旬淋雨的生存境况下,常常,敌机刚离去,人们就从防空洞钻出,立即投入到各自生产和生活中,救死扶伤,生产自救……支援抗战,像号角,在歌乐山、在渝州半岛的各个角落悄然奏响。团结,奋进;民族,国家;不要战争,呼唤和平……在市民内心如铜墙铁壁悄无声息地树立起来。但人们的内心深处,总是不平静和压抑,有股血流在奔涌,既有对侵略者的恨,也有对抵御侵略的勇,于是,“黑云压城”般的山峦与迷蒙夜雨,既是对巴蜀自然地貌的写实,亦隐喻战时中国的压抑氛围。此情此景,苍茫混沌的意境,正如当时抗战时期的艰难险阻,由此,将自然景观转化为民族苦难的象征载体,慢慢在画家心灵深处悄悄发芽。
于是,借李商隐《夜雨寄北》诗意入画,既取其意又突破古典隐逸情怀,还用左下角江面“隐约的樯桅”象征画家的漂泊孤旅,而画作中山间微光小径与酒肆,则暗含对和平生活的渴盼,形成“身处困境却向往光明”的精神抗争。国难当头,人处他乡,既忧国,又忧已,家国情怀激烈地占据着画家的思想,如一股宏大的澎湃力量,势必要宣泄而出,手握画笔,挥毫泼墨,《巴山夜雨》便由此产生了。
其次,《巴山夜雨》是动荡时代的文化符号,双重抗争的意象呈现
同年,傅抱石先生看到日本《改造》杂志上横山大观的一篇题为《日本美术的精神》的文字,对其中称对华宣战是所谓的“圣战”言论十分不满,一下点燃他爱国的激情和热忱。作为艺术家的他,便慷慨激昂地撰写出《从中国美术的精神上来看抗战的必胜》一文,反戈一击,文中鲜明地提出“中国美术”是“日本美术的母亲”的精辟论述,并指出中国美术有三种伟大的精神:“第一,中国美术最重作者人格的修养;第二,中国美术在与外族、外国的交接上,最能吸收、同时又最能抵抗;第三,中国美术的表现,是‘雄浑’、‘朴茂’,如天马行空,夭娇不群,含有沉着的、潜行的积极性。这三种特性,扩展到全民的民族抗战上,便是胜利的因素。”通过学术研究来论证“中国美术的精神,日本是不足为敌的”,从一个侧面鼓舞了抗战时期国人的信心。
都说:文如其人,画彰其心。画作作为艺术表现形式,便是画家内心思想情愫的真情表白,无论是歌咏,赞美,还是鞭挞,抨击,傅抱石先生都展现得淋漓尽致。责任,担当,气节,透过他羸瘦的外表宣露无遗。
许,山城重庆,这个不算太平的陪都,让画家内心有股激荡的奔涌之情。
此时,他以现实为题材,以生活为场景,融巴山夜雨的情趣,撷钟灵毓秀的面容,将秀丽与水墨揉碎,通过山城重庆的地域地貌,浓墨重彩地溢于笔端。无论是宏伟彰显的盛大气魄,还是水墨晕染的气韵,抒发山水之神韵,表达热烈喷薄的民族豪情,都是傅抱石先生在重庆期间创立山水画风的精彩呈现。
至1943年,傅先生创作出的山水画《巴山夜雨》便成石破天惊的代表作。此画作,既写实,又重景,更有意与理的融合,将现实与深刻的思想融会贯通,有山城的地貌,有水墨的韵致,有磅礴的气势,有积极的隐含之喻意。
整幅画面大半布置成重重的山峦,形成铺天盖地泰山压顶之势,但在这一大块如“黑云压城”般的“结构”里,画面给人感觉是破笔散锋大胆而来,连皴带擦,营造出天地一体,苍茫混沌,然后再加以渲染,把线和皴统一成面,将整幅画面的调子和谐起来,于是山水云雾揉合在一起,有层次,有脉络,成就了一个无比丰富的世界;用笔上豪放张扬,以浓墨重写,却能表现雨中朦胧夜色,山上房舍层层叠叠,画来似不经意而山城雄姿却充分展现;画法新颖奇特,以淡墨斜扫画面,寥寥几笔,却出神入化,入木三分。
画面下方的一间小屋里,隐隐透出亮光,正是画家与夫人在秉烛夜谈;山的高处有一小径,是画家授学的必由之路,而山腰又有平素常去打酒小酌的小店,这些现实生活中的元素都是渗透到傅抱石先生血液中的熟悉景象,在这个下雨的秋夜爆涌笔端,正是画家情感思想“爆发”的雄奇诗篇。
第三,《巴山夜雨》是动荡时代的文化灯盏,对艺术商品化的抵抗
一方面是对日本美术话语的反击。傅抱石通过撰文驳斥日本“圣战”论,提出的“中国美术是日本美术之母”观点如一盏明灯,体现到《巴山夜雨》中天地一体的混沌美学,正是其主张的“中国美术雄浑朴茂精神”的视觉实践。画面拒绝日式浮世绘的装饰性,以恢弘水墨重构东方美学话语权,成为文化自信的无声宣言。
另一方面是对艺术商品化的抵抗。抗战时期重庆画展兴盛,但傅抱石拒绝媚俗笔墨。此作以“诗画互文”深化思想性,如题跋所言:“与时慧纵谈流徙之迹,因商量营此图为纪念”,将个人记忆植入民族集体叙事,抵制了艺术市场的功利化倾向。
过去,我们学习鲁讯先生的文章时,老师都会再三强调:注意领会文中极其深刻的内涵。如《灯下漫笔》中揭露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的循环……如此地理解,先生的画与鲁讯的文是否有异曲同工之妙?
那么,《巴山夜雨》中那重重的山,密云众生的雾,层层叠叠的房舍,烟雨弥漫的夜色,小径,酒肆,黎明前的灯光,虚虚实实的线条,皴墨等等,如果以文字来解读,便有象征,有隐喻,是托物而言志的精彩篇章,是东方美学思想的有力呈现。回归到抗战胜利前的那一刻,《巴山夜雨》就是一曲鼓舞人心的抗战必胜的歌谣。
如今,国画大师傅抱石先生《巴山夜雨》的旷世名作,已以3220万人民币成功拍卖,天价的画有着无尽的艺术芳华。今天,国家昌盛,人民幸福,但“牢记历史,珍爱和平”的警示与激励如她的艺术生命一样永远闪烁着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