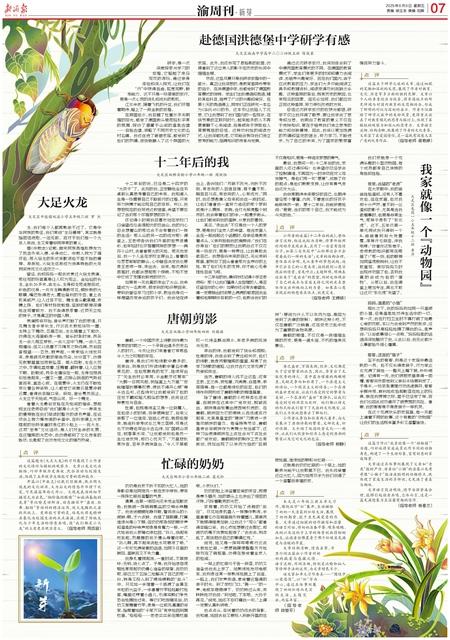A8:渝周刊·龙水湖
□杨福成(山东)
素民生活,很多日子都看似相似,其实,生活中的每一天都是仅有的日子,它们从不重复,也不会重复。
日子,是每人每日二十四个钟点。有人嫌其太多,有人恨其太少,而日子依旧不紧不慢地踱着方步,从东到西,从生到死。
山下的一位老人,每天坐在巷口的石凳上,数着日子。他数得很仔细,仿佛在数着口袋里的铜板,生怕少了一个。他的手指枯瘦,关节突出,在空气中点着,一、二、三……数到第一百零三天时,他忽然停住了,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惊慌。原来他记不清昨天是否数过了。于是他又从头开始数起。如此反复,竟成了他每日的功课。邻居们笑他痴,我却觉得他比许多人都明白——日子是经不起数的,一数就乱了,一乱就少了。
我的一位朋友,日夜伏案工作,眼睛熬得通红。他说要趁年轻时多挣些钱,将来好享福。我问他何为“将来”,他愣了一愣,继而笑道:“将来就是以后的日子啊。”我便不再言语。他大约以为日子是可以储存的,像谷子一样囤积在仓里,待到冬日慢慢享用。殊不知日子是最不耐储藏的,今天的太阳晒不干明天的衣裳。
菜市场有个卖豆腐的妇人,每日天不亮就起来磨豆子。她的手上长满了茧,脸上刻着深深的皱纹,却总是笑着。我问她为何如此高兴,她说:“每天能起来做豆腐就是福气。”她不懂什么大道理,却知道每个早晨都是白捡的,多一个就是赚一个。她的豆腐做得极好,又白又嫩,仿佛把日子的精华都凝在了里面。
日子之于人,大抵有三种态度。
其一如守财奴,将每个日子都锁在铁箱里,舍不得用,到头来打开一看,里面空空如也,连灰尘都不曾留下。我曾认识一个富商,家财万贯,却吝啬度日,连阳光都要算计着用——上午在东窗看书,下午便移到西窗,为的是省下电钱。后来他死了,儿子发现他的账本上记满了节省下来的时辰,却不知这些时辰都去了何处。
其二如败家子,将日子大把挥霍,今日有酒今日醉,明日愁来明日当。街角的酒馆里常有这样的主顾,喝得烂醉如泥,嘴里嚷着“人生苦短”。他们以为自己在享受生活,实则是在溺毙光阴。酒醒后,日子已经溜走了许多,而他们却浑然不觉。
其三如园丁,知道日子如种子,埋下去不见得都能发芽,但若不埋,便绝无收获的可能。我的邻居,每日清晨必在院中读书一小时,雷打不动。他说这一小时是他的“私蓄”,存的是智慧,利的是心灵。几十年下来,他的学问竟比那些整日埋头苦读的人还要深厚。原来日子也欺软怕硬,你认真待它,它便厚报于你;你轻视它,它便加倍地报复。
日子是最公平的,给乞丐和皇帝的一样多;日子又是最不公平的,同样的时辰,在不同人手里竟能变出不同的花样来。有人能将一日拉长如年,有人却使一年短如一瞬。
医院里的病人最懂日子的珍贵。我在医院陪父亲时,一位垂危的病人拉着我的手说:“我现在才明白,日子不是用来数的,而是用来活的。”他的眼睛亮得出奇,仿佛要把所有的光都吸纳进去。第二天他便走了,临终前还望着窗外的阳光,眼神里满是不舍。那一刻我忽然懂得,所谓“仅有的日子”,不是指数量的多少,而是指质量的厚薄。
乡下人比城里人更会过日子。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看天吃饭,随季节变换活计。他们不争分夺秒,却也不虚度光阴。
城里人发明了许多节省时间的机器,却越发觉得时间不够用。他们把日子切成碎片,用在这里一点,用在那里一点,到头来却发现什么都没留下。电子日历提醒着每个约会,手机闹钟催促着每项任务,人成了时间的奴隶而非主人。我常想,那些被省下来的时间都去了哪里?或许它们根本不曾存在过。
孩子们对日子最有悟性。他们可以为一朵花驻足半天,为一只蚂蚁蹲上整个下午。在他们眼里,每个时辰都是新的,充满无限可能。一位小朋友曾经问我:“为什么大人们总是看表?”我竟无言以对。是啊,我们为何总是看表?是为了追赶时间,还是为了确认自己尚未被时间抛弃?
读书累了,我常想起那些已经逝去的日子。它们有的明亮如昼,有的黑暗如夜,有的平淡如水,有的浓烈如酒。它们组成了我的生命,而我却记不清大多数日子的模样。
人生的日子,用掉一个便少一个。所谓“仅有的日子”,不是警示我们时日无多,而是提醒我们,每个日子都不可替代。今日的太阳与昨日的不同,明日的风雨也与今日的迥异。
日子是仅有的,但意义是人给的。你可以把它过成囚笼,也可以把它活成翅膀,全在一念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