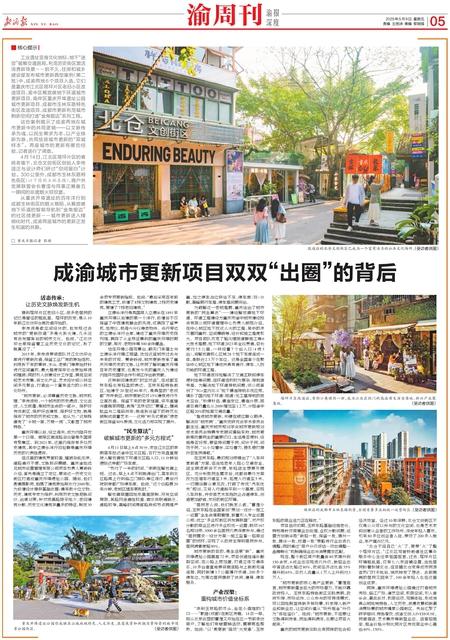A8:渝周刊·龙水湖
□周康平(重庆)
我从小生长在一条爬坡上坎中望不到尽头的千年老街。对于在那条老街长大的我来说,让我时常想起的,多半不是那条千年老街,而是在老街摆摊的王二。
我家与王二是邻居。三十多岁的王二,个子不高,瘦脸,细眼睛。王二是他的大名,老街里的人,通常不叫他王二,而是喊他补锅匠。这叫法听上去不太文雅,但是,喊他的人,没有一点儿歧视的意味,反倒包含了一种羡慕之情。确凿地说,人们羡慕的不是王二这个人,而是他的补锅手艺。会这门手艺的,别说在我们镇上,就是在周边的几个乡镇,也找不出第二个有他这般手艺的人。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话不仅是我们那个年代的生活写照,更是王二每天补锅的生动诠释。王二的补锅摊子,看上去很是简陋,补锅摊子摆在他家的木门边上。一个铁皮工具箱,一个小炉子,一口坩埚,一个布满煤灰的小风箱,加上两条供客人落座的长板凳,便是王二的补锅摊子了。
人们拿去修补的铁锅,常见的一般都是像绿豆或胡豆一般大小的破洞。这种让人毫无办法的破洞,在王二的眼里,只是小菜一碟。
王二举起放在摊子边上的铁锅,锅底朝天,面对光亮,眯着眼睛,查看起铁锅上面损坏的情况。找准破洞的王二,拿起一张磨砂纸,在破洞的周围搓擦起来,然后用嘴在洞眼边上吹了吹,再用干布擦拭几下,往坩埚里扔上几块生铁,呼呼地拉起与小炉子相连接的风箱,待坩埚里的生铁变成滚烫的铁水时,王二将坩埚里的铁水倒在一块厚实的黄泥膏上。这是一块略微呈凹陷状的黄泥膏,通红的铁水在黄泥膏上面轻微晃动,我看着就胆战心惊,要是铁水滚到手上,怎么办!当然,我的担心只是多余,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只见王二手握黄泥膏,娴熟地将黄泥膏上的铁水,稳稳地贴在锅底的破洞上,铁锅里面立即出现一团火红,只是瞬间,铁水与铁锅就紧紧地粘在一起。与此同时,王二用右手将圆柱状的湿棉球,在破洞上下左右擦拭起来,随着冒起一阵青烟,铁水完全凝固在破洞上。待冷却后,王二再用砂子和湿布,在修补的地方反复擦拭,一口可以重新做饭炒菜的铁锅,就交到顾客的手上。
王二除了补铁锅,也补铝锅。铁锅是热补,铝锅则是冷补。补铝锅与补铁锅,有着明显的不同。铝锅的锅底,哪怕只有沙粒般的洞眼,也得换底,如此,修补的成本也比补铁锅贵出许多。
铝锅换底,对王二来说,就是把铝锅抱在怀里,拿起一把大缠着蓝布把柄的大剪刀,沿着锅底边大约两三公分高的地方,剪开一小口子,用力剪去。这是一个需要手劲的活,王二握着剪刀的手指,手关节紧绷,手背上凸起的青筋如蚯蚓般清晰可见。剪刀剪铝锅底,带着脆生生的响声,给人的感觉,像剪刀剪纸那般舒适。剪去坏了的锅底,扣上一个崭新的锅底,放在一字马的铁架上,按着锅底,用锃亮的小号铁锤,沿着锅底衔接处的边缘,一边敲打,一边旋转,叮咚地敲打不停。大约二三十分钟后,一个严丝合缝的铝锅换底,就完成了。
在我的记忆里,王二每个月也补不上两三个铝锅。人们拿去补的锅,绝大多数是铁锅。铝锅也好,铁锅也罢,这些在王二手里修补的锅,不仅是他的收入来源,更是他平时骄傲的资本。王二曾自豪地对围在他摊子边的人说,我们镇子周边几十里地的人户,有几家吃饭的锅,与他王二没关系?王二说的是实话,没有吹牛的成分。在那个年代,我们谁家的铁锅,没坏过呢。谁家的铁锅,又没上他那儿修补过。如今,补锅这行当虽然早已消失,老街补锅摊的一些画面,却时常在我心里闪现,毕竟,那是一个时代的鲜活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