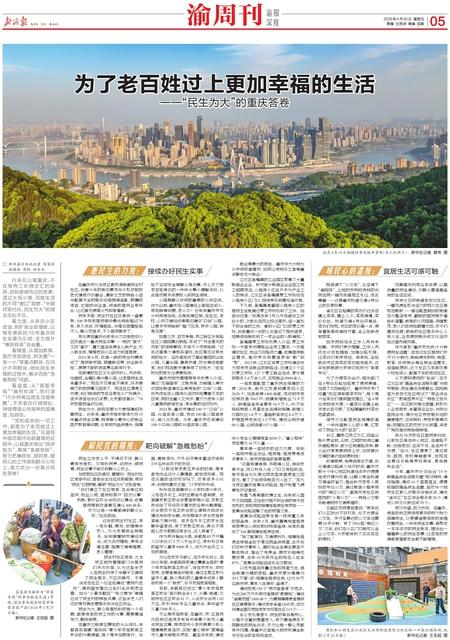A8:渝周刊·龙水湖
□杨福成(山东)
世间有一种东西,叫作雅物。
何为雅物?大约不过是些瓶瓶罐罐,书画琴棋之类。然而人们每每见了,便觉得心神为之一爽,仿佛胸中块垒,被那雅物轻轻一拂,便消尽了。
我见过许多雅物。有青瓷碗,釉色如雨过天青;有紫砂壶,形制若老僧入定;有古琴一张,桐木纹理间似乎藏着前朝的音律;有残帖半幅,纸色昏黄而墨迹犹鲜。
这些物件,静静地躺在玻璃柜中,或是挂在粉壁上,向来是默默无闻的。然而一旦被人瞥见,便忽地活了过来,与那看客的目光相接,竟至于生出些言语来。
雅物之雅,多半不在其本身。一只土窑烧出的粗碗,若经了名人之手,便陡然身价百倍;一块顽石,若有文人题咏,便顿成珍宝。人们所追逐的,其实是附在雅物上的那些看不见的东西——岁月、名声、传说。雅物不过是盛装风雅的器皿罢了。
我曾在一个收藏家府上,见过一只定窑白瓷瓶。那瓶通体素白,无一丝纹饰,形制亦极简。收藏家双手捧出,置于黑檀几上,室内灯光便在那瓶身上流泻如水。
他道此瓶乃北宋遗物,传世仅此一件。我细看那瓶,果然胎骨轻薄,釉色莹润,确非凡品。然而更令我惊异的,是那收藏家的神情——他凝视瓷瓶的目光,竟如瞻仰神一般虔诚。
瓷瓶不过是瓷瓶,而人却将自己的精神,全数灌注于这无生命的物件上了。
雅物之于人,有时竟成了枷锁。
我认得一位老先生,平生最爱收集古墨。他家中专辟一室,四壁皆是楠木橱柜,内分数格,每格贮墨一笏。那墨有松烟的,有桐油的,有漆烟的,形状或长或方,或圆或扁,上面模印着各种花纹题识。
老先生每日必入此室,将那些墨一一取出,摩挲品鉴,自谓得人生至乐。后来他病重,犹念念不忘那些古墨,嘱咐家人务必善加保管。他死后,子孙争夺遗产,那满室古墨竟不知所终。
人以为在玩物,实则被物所玩,此之谓也。
然而雅物亦自有其生命。它们从匠人手中诞生,历经无数人之手,看尽人间冷暖,而依然保持着自己的品格。
一只明式黄花梨圈椅,不论置于朱门绣户还是蓬门陋室,总是那般挺拔清峻;一方端砚,不论用来挥毫万字还是镇纸压书,总是那般温润如玉。
雅物之雅,正在于这种不为外物所移的定力。
记得某年冬日,我在中山公园一家旧书店中,偶然觅得一部残缺的《水经注》。书是木刻的,纸已黄脆,边角多有虫蛀。
店主人是个须发皆白的老者,见我翻阅此书,便道:“此书虽残,却是康熙年间的刻本,世间存留无几了。”我问他价钱,他竖起三根手指。“三十元?”我问道。他摇头。“三百?”他还是摇头。我正疑惑间,他开口道:“三块钱。这书虽老,终究是残了,不值什么。况且如今识货的人少,与其让它在这里蒙尘,不如交给懂得珍惜的人。”我付钱取书,心中却比得了什么珍宝还要欢喜。
这老店主,才是真正懂得雅物之道的。
世人常将雅物与金钱等量齐观。拍卖会上,一只成化斗彩鸡缸杯可值亿万;画廊里,一幅名家字画能抵半城。然而真正的雅,其实是金钱买不来的。那位旧书店的老主人,明知那部残本《水经注》价值不菲,却只收三块钱,这便是雅。
雅是一种态度,一种超脱于物质之外的精神。
我见过一个茶人,家徒四壁,唯有一把朱泥小壶相伴。那壶形制平平,并非名工所制,但因常年泡养,壶身已呈温润光泽。
茶人每日早起,必先以清水涤壶,然后沏茶自饮。有人出高价求购此壶,茶人笑而不答。后来他病逝,那壶竟不知所终。有人说壶随葬了,也有人说壶被其弟子携去远方。
我想,无论那壶身在何处,它所承载的那份从容淡泊,已经超越了器物本身的价值。
雅物之所以为雅,全在于人心。
同样一把紫砂壶,在茶人手中是雅器,在古董商柜中便是商品,在暴发户架上便成摆设。
物本无雅俗之分,雅俗只在于人。人心雅,则万物皆雅;人心俗,则雅物亦俗。
如今,满街都是“雅集”“清赏”的招牌,人人争说风雅,而真正的雅却愈发稀少了。那些被玻璃罩子保护起来的“雅物”,与动物园笼中的珍禽何异?
雅物本该与人亲近,如今却成了供人瞻仰的偶像,岂不可叹。
真正的雅物,不必是古董珍玩。案头一盏灯,窗前一株梅,架上几卷书,皆可成雅。雅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是对寻常事物的一种珍重态度。
能在平凡中见出不平凡,在简单中体会丰富,这便是雅的开始。
由此说来,雅物,不过是人灵魂的倒影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