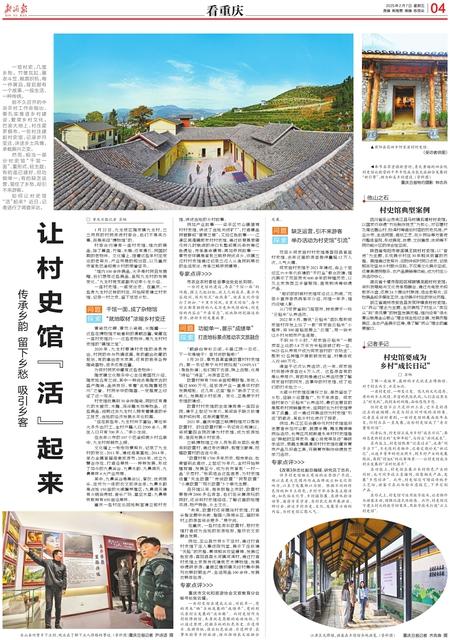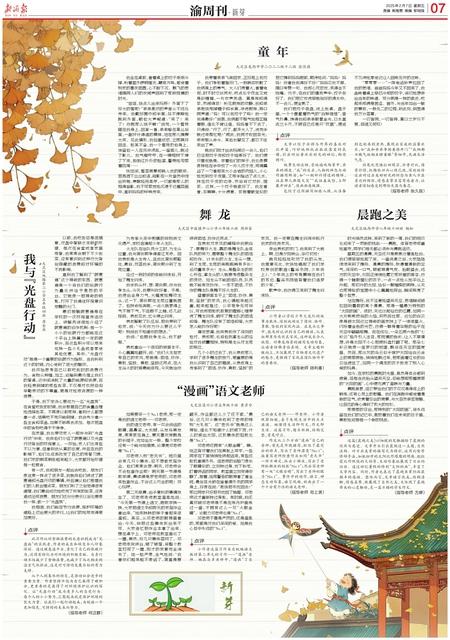A8:渝周刊·龙水湖
□曾广洪(重庆)
黑黢黢的煤炭灶是母亲大舞台,也是这煤炭灶煮甜了我们的日子。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透过窗口照在煤炭灶上,母亲已经开始忙碌起来。她熟练地添煤、扇火,火光跳跃间,一股暖流开始在屋内蔓延。那灶膛里呼呼的火苗声,那冒着热气的大铁锅,还有那母亲灶前灶后忙碌的身影,那被映红了的脸庞,始终无法忘记。无论是盛夏的正午,还是寒冷的冬季,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尽管粗茶淡饭,尽管日子清苦,一家人依然其乐融融,没有抱怨与叹息。
家中有煤炭灶,似乎整个家里就有了生气,日子也变得更加的有滋有味。若是在过年过节或者来客人,随着煤炭灶炊烟飘浮,全家人都知道要打牙祭了,我与大黄狗垂涎三尺,眼睛锁住那稀缺的骨头,就连瓦房上的麻猫都猫视耽耽。有一天,远方的外婆来看我家,母亲开心至极,赶紧煮老腊肉,孰料那可恶的麻猫转瞬间就叼上屋脊尽情享用,父亲拿竹竿捅也鞭长莫及。母亲急得跺脚也无济于事,只好煮两个盐蛋应急。慈眉善眼的母亲思量再三,终于给我下达了追杀令,布下陷阱没几天功夫,那只贪吃猫就付出了代价。
中午,太阳懒洋洋地挂在天空,家家户户开始做午饭,整个老街飘着人间烟火气息。在那缺衣少吃的大背景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8岁时就跟母亲打下手学煮饭了。煤炭灶与柴灶连为一体,高近3尺长5尺许,由灶膛、炉孔、灶门、炉桥、烟囱等组成。灶台系青石板扣成,煤炭、小铲、火钩、火钳一应俱全,依次摆放。煤炭灶看似简陋粗糙,若想驾轻就熟,也绝非易事,操作难度与如今的天然气灶有天壤之别,就像平时开惯了自动档车突然改开手动档车,让你手忙脚乱,非出洋相不可。
但凡烧过煤炭灶的人皆知其操作技巧。先点燃干树叶或废纸引燃中层的柴禾,把拇指大小的煤粒轻轻放在上端,再用蒲扇助燃。如柴禾受潮湿润,一时半会无法点燃,你干着急也无用。倘若引火柴少了,更不会点燃煤炭。要是烟囱不通泰,倒烟会把你熏得像黄鼠狼似的狼狈。烧煤炭灶得有丰富的经验,随时都要添煤、漏灰、夹矸石、开关风门等。不然的话,炉火像鬼火,煮出“夹生饭”来。有时稍不留神,炉膛的火就熄了。煤炭黑如墨,经常把我的脸弄成大花猫。火钩漏灰时,灰尘四起,直钻鼻孔。特别在三伏天做饭,如同炼丹,一顿饭菜做下来后,汗水直淌。
巧媳妇难做无米之炊,煤炭灶用起是否顺当,与煤炭的优劣有直接关系。当地人慧眼识真金,一眼就能区分出煤炭的三六九等。燕子岩煤窑的“打铁炭”,指头粗细,六菱状,黑得发亮,接火快、火力猛,遗憾的是价格贵得咂舌。最麻人的是“梭壳子”煤炭,外表油光水滑,实则马屎皮面光,里面一包糠,着火慢、矸石夹中间。山里人敦厚朴素,最瞧不起华而不实之徒,要是哪个被冠以“梭壳子”的歪号,那小子找老婆都成问题。而火烧湾煤窑的和生炭最受欢迎,性价比特高,点火快又熬火化渣,还可以炼焦煤呢。
炉膛在高温下隔三岔五出毛病,父亲糊炉膛自有独门绝活,他在后山挖来黄沙泥,和上水与少许盐巴,搓揉得像面团般的糍糯。他说,黄泥巴糊灶,各师各教。父亲糊的炉膛光滑、厚薄适中,既节约煤又耐用。有一天,灶里的炉桥烧断了,饿得我肚子咕咕叫,父亲却念念有词: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
傍晚时分,是煤炭灶最为热闹的时候。母亲贤惠能干,擅长茶饭与针线活,特别是做难得一见传统的“水八碗”,色香味美,闻名乡里,婆姨们时常来拜师学艺。她做饭似乎从来不要父亲去帮忙,母亲忙着煮饭时,也是父亲闲暇时刻,他会坐下来抽袋烟,那是属于他的片刻宁静。父亲在解放初参加解放军,淘得几手厨艺,退伍后任公社武装部长。他兴趣浓时,来几句《智取威虎山》,抑或取下二胡拉上《洪湖水呀浪打浪》。当然,每逢过节或珍贵客人来访,他系上围腰下厨做最拿手的血旺汤与爆炒猪肝。
如今,尽管我已步入花甲之年,但那烧煤炭灶的场景仿佛发生在昨天。在那炊烟升起之处,是温馨家的符号与母爱的象征,也是幸福的欢欣,更是清苦日子里的宁静。有时候,在夕阳西下、倦鸟归巢之际,我站在山岗上,眺望老街炊烟缭绕,那朦朦胧胧的感觉,恰似一幅人间烟火气意境的写照。母亲那“只要煤炭灶还在冒青烟,我们曾家就有盼头”的话言仍旧回响在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