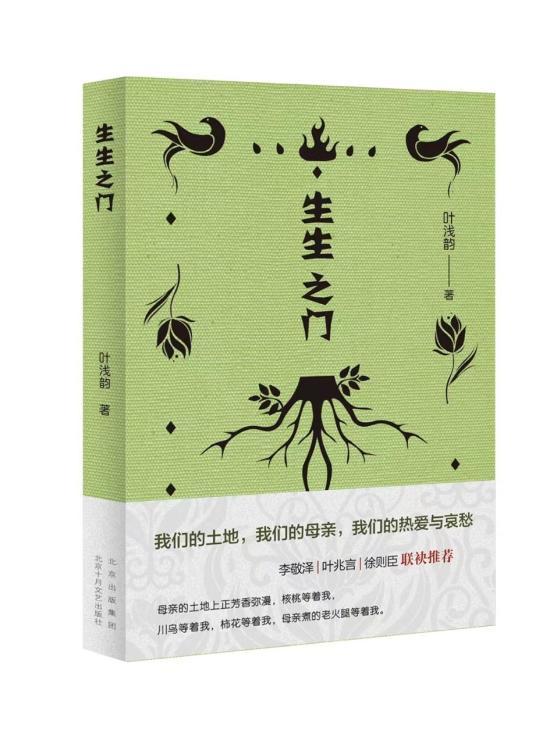A7:渝周刊·读书
□董运生 廖敏
人只有到了一定年龄,经历了岁月的打磨之后,才会对生活乃至生命,形成具有一定深度的思索与体悟。由春末到夏初,我断断续续读了三遍散文集《生生之门》,被叶浅韵的真诚与勇敢,被作品对苦难的正视与超越深深感动着。我相信,对土地的深情,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的审视是会传染的,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共情或共鸣。
《周易》有言:“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从首篇《生生之门》到尾篇《生生之水》,“生生”是作品的关键词,究其立意,是对生命存在的关注与审视。我们都在生活着,但对于生命的意义却很少予以反思与表达。《左传》有言:“天生五材,民并用之。”木、火、土、金、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视为构成世界的基本元素,事物的发展变化是五行相生相克的结果。如作者所说,“金、木、水、火、土这五种元素在有形和无形之间,都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生产生活,而且在每一个地方都有时代和个人生活交叠的痛点”。它们既给人类的生活提供了物质保障和精神寄托,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的苦难和考验。在一定意义上说,人类的历史,就是在不断利用这些资源并克服伴随它们而生的诸种矛盾中前进的。
天地最大的德行是生命的赐予,有了生命,才有了生生不息的生活。意义是伴随着人类生命的诞生而产生的,跨过生命之门,才会有对存在的记录、审视与表达。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而水又常被视作生命的源泉。故而从第一篇《生生之门》到第六篇《生生之水》,整部作品可以视为一个闭环的结构。其中的每一篇都相对独立,一个个小故事如一颗颗珠子般串联在一起,述说着生生之力、生生之苦、生生之美;篇与篇之间又兼容并蓄、掩映勾连,形成一个紧密的有机体。故而,整部作品可视作一长串珠子,分层环绕在“四平村”人的手腕之上,一个故事是一颗珠子,一篇故事如一个圈层,首尾相连、次第转旋。
《生生之门》是一本关于作者生长之地“四平村”的新乡土写作。叶浅韵以生命体验的在场和女性特有的细腻,呈示着村庄的风土人情、时代变迁、困苦喜乐。不少作家都努力建构着自己的文学故乡,无论是沈从文的湘西,贾平凹的商州,还是迟子建的北极村,叶浅韵的“四平村”,故乡既是他们生命的发源地,也是他们精神的成长地,更是他们离开之后建构起来的一种文学想象。叶浅韵的“四平村”里盘结着昔日生活的根系,也吹拂着新时代的风气,在“四平村”人的家长里短、俗常生活中,蕴蓄着叶浅韵带着生命印痕的审视与反思。作者对“四平村”的情感是复杂的,既有对真、善、美的高扬,也有对假、恶、丑的批判。带着生命温度的真情呈现与深刻真诚的审视反思,使作品在热情与理性的激荡间增加了弹性、张力与深度。
在《生生之门》中,叶浅韵选择了一种以“四平村”人讲“四平村”日常生活的叙事姿态与策略。作品中的事件,从妇女的生产、房屋的修建,到村庄的火灾、土地的纠葛、吃水的困难等,大多是乡村生活中的俗常小事。民间立场的选择,使作品充满了烟火气息。作者没有以启蒙者的眼光打量和批判乡村,也没有站在离乡者的角度回忆乡村的美好,而是以亲历者、见证者的姿态记录乡村的凡常生活,于村人的哀乐悲欢中叩问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这里以开篇二伯母生产相关的故事为例。二伯母痛苦的呻吟使家中的气氛变得有些奇怪,爷爷撬了大门的门槛,说是向神仙投降以表诚心;二伯没有请到接生婆却请回来了个神汉,在奶奶的责问中,总算结巴着把想要表达的意思完整地表达了出来;生儿子的第二天早晨,二伯抱着一只红公鸡去给丈母娘家报喜去了。相关场景和情节,既反映了特定时期农村的社会思想状况与民风民俗,也以简短的文字塑造出了鲜明的人物形象,然而作者并没有停留于此,全家人沉浸在添了男丁的喜悦之中,二伯母刚从鬼门关打了一个转儿的事情,倒是被大家冷落了。喜与悲的反转,生与死的对比,男与女的差别,人性的美与丑,人情的冷与暖,都源源不断地从中溢出,化作无声的愤怒与拷问。二伯母生了儿子,对于一个家庭的香火传递功莫大焉,然而,她在家中的地位也不过是高出了“一篾片”。深重的苦难与单薄的篾片悬殊巨大,相形之下,女性的地位、价值、命运等一系列问题绵绵涌来,引人深思。
接地气的散文,都是与时代拥抱中开出的花朵。《生生之门》中的六篇散文贯通今昔,将个人、群体、时代、家国联系起来,以此来展开对生命的追问。如在首篇文章中,作者将女性的身体看作生死场,以祖母、二伯母、五伯母、自己等人的生育经历,将传统社会、计划生育、放开二胎三个时期贯穿起来,将女性的生育与家庭、社会、国家勾连起来,放置在宏阔的历史场景中予以审视,既展现了女性生育活动中生理的痛楚与精神的折磨,也淋漓地彰显了作者的使命意识与生命关怀。如作者所言,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在传统文化、习俗的重压之下,个人的声音也许是微弱的,“但身为一个女性写作者,我无法忽视同类的生存状态。”
“修辞立其诚”是重要的中国文学传统,在《生生之门》中,作者用真诚、勇毅的眼光审视、书写生活,尤其是其中的苦难与痛点。作者以直面困苦的姿态讲述生之艰辛,既彰显了生命体验的在场感,也极大地调动了读者对苦难的同情与思考。在《生生之门》中,苦难的场景多有呈现,如女性生产过程中撕裂身心的疼痛,父亲英年早逝而未有一副好的老木头的痛与憾,二舅因幼时烧伤致残而久处底层的悲惨人生,丈夫事业遇挫后的无助与焦虑等,诸种苦难,唯有亲历或近距离接触后,才能写得如此真实与生动。《生生之门》中的六篇作品虽多有触及苦难,但整体写作基调并不消沉,只有正视并勇敢地应对苦难,才能最终与世界和自己释然。
叶浅韵的《生生之门》是一株在泥土中努力向着天空生长的格桑花,虽充满形而下的烟火气息,却也常常从中升腾起形而上的生命之思。书中的诸多苦痛遭遇,如一根根鼓槌敲击着读者的心门,期待着响起一阵阵心灵的回声。生活中的那些苦楚,串联起一串串追问生命的足迹,通向遥远而又令人困惑的人生、命运。在穿透事实的思考与追问中,我们看到了人性的智慧与光芒。正视生命、超越困苦,才有可能对“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个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交出满意的答卷。如在《生生之土》中,作者抚今追昔,于认识到土地的变迁是一部人类生存史和精神史后指出:“土地和母亲,都是人类生生不息的母体。只愿我们在挣脱她的怀抱时,眼中还有慈爱,心中还有敬畏。迟早有一天,我也要成为土地的一部分。如今,我的身体正在向大地弯曲。我努力地活着,像母亲那样,做一个热爱土地的人。以期让自己有一天成为土地的一部分时,能与土地的干净相匹配。”
在《生生之门》中对苦难的叙写背后,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对光明的追寻与自我的疗愈。生活总会在给我们关闭了一道道门的同时,又打开一扇扇窗。女性生育的身心之痛,父亲早逝的苦痛记忆,金钱对人性之丑的催化,作者对这些故事的呈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视作一种书写表达,借披露、表达与个人有关的经历与感受,来实现自我心灵的疗愈。写作的过程,是舒缓心中压抑、焦虑情绪的过程,也是自己与社会、他人、世界和解的过程。叶浅韵在《悬在针尖上的命》中曾说:“文字已然成为我生命的出口,我通过它抵达我想要的初地,在文字里修篱种菊,与文字信誓旦旦,让文字插上飞翔的翅膀,飞过荒漠和人烟,飞过欢喜与哀伤。”
《生生之门》的文字散发着一种带有野性的活力。维特根斯坦曾说过:“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方式。”在作品中,叶浅韵较大程度地保留着那块土地上长出来的日常语言,并将其与较为规范的书面语言混合,建造起了一座活生生的关于“四平村”人的生活大厦。带有相当大陌生化色彩的地方语言,虽与普通话及不少读者的地方语拉开了较大距离,但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找到那把打开“四平村”生活大门的密钥,走进村人的喜怒哀乐。奶奶爱说的“苦荞粑粑才动边”中,有一个地域的作物种植和饮食习惯,也有着一方农人的困苦与坚韧。“跳脚米线”“苦钱”“方圆团转”“鞋歪脚踩”“血滴滴”等诸多方言语汇的运用,使作品发散出一股浓重的地域气息,也彰显了作者对生养自己土地的恋恋深情。
就文体而言,《生生之门》可视为大散文写作的一种新探索。不少人对体量较大的“文化大散文”“历史大散文”并不陌生,这些作品对满足读者文化和审美需求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叹服其厚重的同时,我们也时常会发现烟火气息的稀薄与读者群体的窄化,尤其是在生活节奏加快、碎片化阅读盛行的当下。《生生之门》中的六篇散文均可视为生活大散文,作者以边地女性的独特视角与体验,将一个个细碎的寻常故事串成一串晶莹的珠子,书写“四平村”人生生不息的喜怒苦乐,思考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生生之门》等非虚构生活大散文引起了不少读者的欢迎,这值得我们深思。优秀的生活大散文既要有充满烟火气息的生活底色,也要有使命意识与生命关怀,将个人与群体、生活与时代、欢痛与美善结合起来,带着生命的体温去书写,才有可能开拓出一片大散文写作的新天地。
作家对于自己熟悉又动情的生活,总是充满了热情与厚爱,这为写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警惕由此而来的写作惯性或惰性。回望叶浅韵近年来的作品,它们在给我们触动和感奋的同时,也不免会发现一些题材、手法上的相似之处。作家形成个人独特的风格是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但也要警觉自我的重复。
生活常新,关于生活的思索与表达也时刻常青,期待着叶浅韵在她的“四平村”里,开掘出一片新天地,培育出新的作物与食粮。
《生生之门》中对生命意义的追问,让我想到了林斤澜矮凳桥系列作品中所言的“皮实”,生命的意义,不正在于有韧性地去面对生活的苦痛,在经历了苦难的击打和磨砺之后,我们依然对世界和生活充满热爱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