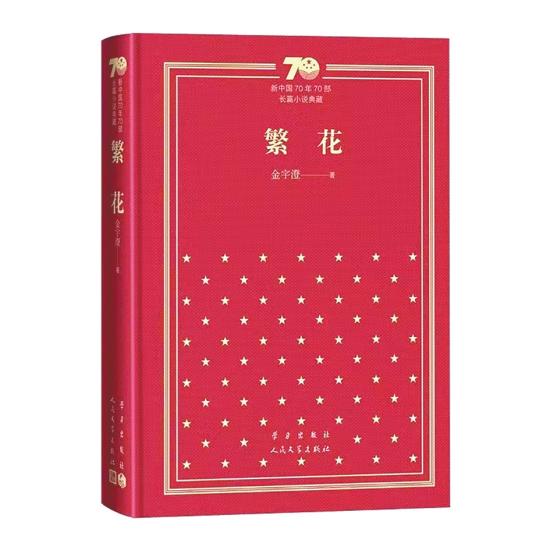A7:渝周刊·读书
□丁东
金宇澄先生2015年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繁花》,被王家卫拍成电视剧后,突然火了。在追剧的同时,为享受纸质阅读带来的沉静和愉悦,我特地上新华书店买了一本《繁花》。读完,觉得金宇澄先生这部中式风、上海范的长篇小说,是一本少有的奇书。
《繁花》采用时空交错的写法,一些章节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往后写,一些章节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往后写,两股时间线交替出现,在“今天”汇合,从“过去”一步一步地走到了“现在”。在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和四百页的文字中,作者金宇澄用白描般的手法、用不“煽情”的文字,以及一副道听途说的腔调,似雨点落下,如花瓣展开,像记录历史一样记录了三代上海人的生活琐碎、忧乐喜悲,揭示了上海市民的心灵史、上海的成长史,让读者不由自主沉浸于一座陈旧、光鲜、精致、多元、海派的都市。
从上只角到下只角,从洋房到新村,从石库门到棚户区,从理发店到发廊,从电影到唱片,从外贸到内销,从邮票到股票……人影重重,人生海海。有人体面,有人窝囊;有人发达,有人落魄;有人坚持,有人放弃;有人苟且,有人消失。各色各样的小人物,“拼命往上爬,人人想上来”,希望出现又落空。他们要么在最美好的时候死去,要么让时光削去美,以庸常的面目长长久久地活着。一如繁花,在上海八九十年代的剧烈蜕变中,随风摇曳,花开花落。何其悲情,何其苍凉。
主人公阿宝,年少时在人声嘈杂的国泰电影院门口排队买电影票,在人头攒动的集邮商店门口找人换邮票,在航模商店买材料自己做飞机模型,挤24路电车去看苏州河。长大成人后,有一次患甲肝住院,有幸结识日本商人,做外贸生意发达,变身宝总。最终在机制尚未成熟的“股市风云”中翻盘,被打回原形……时运不济的小毛,少年时被邻居大嫂勾引,母亲为了消除影响,安排他结婚。婚后不久,妻子死于难产。单身多年的小毛,为帮助某未婚先孕女,与其办了假结婚。在患上绝症后,原先隐瞒他病情的家人,为了房子的归属,告知真相,让他提前写下公证。对此,小毛只能无奈苦笑。沪生是个老实人,其女友梅瑞说她喜欢上了阿宝,执意分手,沪生说好。沪生与白萍结婚后,白萍一人移民国外,与他人生子,沪生既不离婚,也不另找他人。对命运,沪生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卖水产的陶陶,是阿宝的“出窠兄弟”。他喜欢吹牛,讲别人的偷情故事,精彩纷呈,好像全是为了欢愉,全是为了白花花的大腿。在遇到所谓的真爱时,抛弃妻儿,与人私奔,结果对方坠楼而死。民警退回女人两本日记,才知隔着肚皮,一颗心是真是假,真的很难讲。
此外,蓓蒂、白萍、李李、汪小姐、小琴、玲子、梅瑞、姝华、菱红、阿婆、爷叔、雪芝、芳妹、康总、范总、金花、葛老师、小江西等,一个个人物和一件件小事,斑驳一片,折射出人性的多面和社会的多元。仿佛走进了一个菜市场,你所见所闻的是,青青的绿叶菜带着泥巴和露水,鱼盆扑溅的水花泛着腥气。生活在大时代的这群小人物,人格独立,精神自由,不奉承,不歌颂,也不逆潮流,反时尚,平视世间一切,努力活在当下。面对世间不得不面对的不平和不公,他们能做的而且一直做着的是——不响。而不响,是上海人的留白,是上海的留白。从中,我们切身感受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矜持、热情、开放、包容、市侩和忧郁,深刻体悟到了上海这座城市深入骨髓、永远不变的文化底蕴、价值观念和精神气质。而这种精神气质,用王安忆的话说,是“它外部的光华总有一些熟腻的庸俗气,还有一些戚容,这些都是生活所洇染的”。
所有这些,我不确定上海人读《繁花》时会共情到何种地步?然而,对于我这位八十年代中期在上海中山北路、曹杨新村附近读大学、课余喜欢到处闲逛、在普陀区金沙江路、闸北区武宁路一带做过四年家教的“60后”来说,直觉感同身受,怀旧情绪油然而生。——当年的上海人,就是这副腔调。他们的孤独,是时代和这座城市的孤独;他们的蜕变,是时代和这座城市的蜕变;他们的成长是时代和这座城市的成长。
以我数十年的阅读经验,在我看来,小说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意义的小说和感受的小说。所谓意义的小说,通常以故事为媒介,阐明道理,在书写中追求某些意义。十九世纪西方现实主义小说多属于此类。所谓感受的小说,不承担教化人心的使命,甚至都无需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仅仅为了传达某种感受而存在。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即是此类小说的典型。用绘画来比拟,意义的小说像是漫画,注重情节,彰显意义;而感受的小说则像是印象派油画,不注重情节和意义,只在乎创作者的所见所感所思。其余的皆交由读者自己去体会,去理解,去感知。
《繁花》应属感受的小说无疑。它放弃心理描写,拒绝追问人物的内心世界,语调既不慷慨激昂,也不义正辞严,只在碎片化的描摹中塑造氛围,传达感受,完成小人物与大时代的相互书写。其中许多叙述,类似“病人之间的互相探问”,不一语道破,不透露底牌。如此,留下空间,让读者自己在充满苦味的生活中找到一丝美感,寻得一块方糖。就如金宇澄自己所说,人生苦短,要紧的是过好自己的日子,没那么多意义,没那么多深奥的雄心。
由《繁花》我发现,就文学创作的现状来说,尤其是小说类别,除了那种无甚滋味的青春小说、武侠小说,拥有一批年轻读者外,能引人注目、产生阅读兴趣的大多是后运动时代的现实主义作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那些经历过文化革命、改革开放等特殊年代,且烙下鲜明时代印记的作者,在写作群体中依然占据着不可撼动的主导地位。如莫言、格非、余华、贾平凹、陈忠实、刘震云、梁晓声、陈彦、金宇澄等。他们亲身的特殊经历与思索,使他们拥有了解释、评价和重述的能力。用刘再复先生的话说,即“我知道自己的本质乃是一个思想者,一个灵魂主权意识很强的思想者,一个把思想的自由表述视为最高尊严的思想者”。而事实上,每一个时代,即便是物联网、机器人、手机AI的新时代,总可以找到一些值得思索的东西。
小说《繁花》是本少有的奇书,除中式风、上海范、市井味、地域性、碎片化等特征外,通篇都是短句子的语言格调,堪称奇特。硬梆梆、干崩崩的方言短句,让不少读者不甚习惯,感觉晦涩。尤其是上海话中的俗语,能看懂的外地人没几个。如:“陶陶笑说,寿头,好故事,为啥要分开讲,我不穿长衫不摇折扇,不是苏州说书,扬州评话《皮五辣子》,硬吊胃口做啥,碰得到这种人,我吃瘪。”对此,在我看来,《繁花》在叙事语言上的尝试,是对新文学的反动,也是其不清不楚的个性、意义和语言魅力所在。因为剔除了常见修饰语与关系词的短句,此一种特定的语言叙事,能让上海范更足,上海腔更浓,让上海文化更接地气、更具灵性。倘若用通常的语言叙事,《繁花》这本书大抵也就不存在了。
《繁花》通过小人物与大时代的相互书写,写尽苍苍人世。它是一部需要调动全身感官去阅读的小说,读懂《繁花》,就读懂了一个时代的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