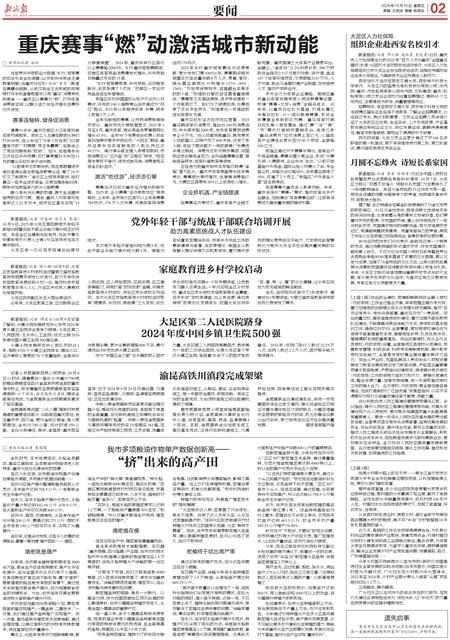A4:龙水湖
□施崇伟(重庆)
到底还是来了。在五十八岁的秋天,由两个年轻的生命牵引着,踏上了这片念叨半生的高地。
昌都的清晨,澜沧江裹着晨光,在城下打了个弯,继续不慌不忙地南行。雨季后水是浑黄的,却并不像此前看过的涨水时的匆忙,沉静得很,仿佛见惯了世面。江岸上,灯火深处,陈二妹的餐馆并没急着打烊。她在有条不紊地接待客人的间隙,坐下来陪我们喝啤酒,打听我们从家乡带来的消息。热腾腾的锅气混着麻辣味飘出来,麻辣着此起彼伏的话题。她点一支烟,说起十年间从卖菜到开店的种种,语气淡得像在讲别人的故事。“闲下来就心慌”,她说。江水汤汤,映着这些异乡人的脸庞,他们在此处扎下根,把日子过得如这江水一般,自有其奔流的章法。澜沧江教给我的第一课,原是这般:净土不在远方,而在人声鼎沸处,那颗认真过活的心。
路是往上攀的,攀到业拉山口,云朵竟落在了脚下。可心还悬着,因那传说中的七十二道拐,就在眼前了。下山的路,是大地一道紧蹙的眉峰。车子成了甲虫,在无尽的“之”字书写行间里小心翼翼地盘旋。赵斌不言,只将方向盘打得飞快,左一圈,右一圈,仿佛在与山神对弈。我不敢看窗外深渊,只死死盯住仪表盘上跳动的水温指针。待到谷底,怒江的咆哮便猛地塞满了耳朵。那水是浑浊的,愤怒的,挟着雷霆万钧之势,要将千山万壑都劈开似的。过桥时,鸣笛声忽然旋乐般响起,一声声,短促而郑重。同行的年轻人说,这是在向修桥的烈士致意。笛声落进江涛里,瞬间便被卷走了,可那份肃穆,却沉沉地压在了心上。这怒江,它教我懂得,我们走得这般容易的路,原是前人用性命铺就的敬仰。
终于到了林芝,海拔回归可以让心平静的刻度,雅鲁藏布江又是另一番气象了。江面开阔,水流虽急,却透着一种从容的气度。藏族小伙阿黑哥引我们到一处高坡,指着对岸云雾缭绕处,“那里,便是南迦巴瓦。”话音未落,一阵风来,那团纠缠的云雾竟似幕布般缓缓拉开,雪白的峰顶在阳光下露出真容,清冷,圣洁,美得令人屏息。也就在那时,我听见了,在江水的轰鸣底下,另一种声音,沉稳而有力,是来自雅江电站工地的机器轰鸣。古老的神山与现代化的工程,就这般无言地对望着。我忽然明白了,这最后的馈赠是什么:净土并非一成不变,它也在呼吸,在生长。那轰鸣声,不是打扰,而是希望,是这片土地走向未来的、有力的心跳。
当布达拉宫的金顶终于在视野里浮现,拉萨河泛着细碎的金光。宫墙下,那些磕长头的信徒,用身体丈量过千山万水而来。他们的额上沾着尘土,眼底却亮着星辰。我忽然懂得,每条江都有它的源头,每个人都有他的皈依。澜沧江教会我生活的温度,怒江让我看见牺牲的重量,雅鲁藏布江指给我未来的方向。而这一路的江水,最终都汇成了眼前的拉萨河——它静静地流淌,映照着千年宫墙,也映照着一个老人圆梦的身影。原来所有的跋涉,都是为了抵达内心的这片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