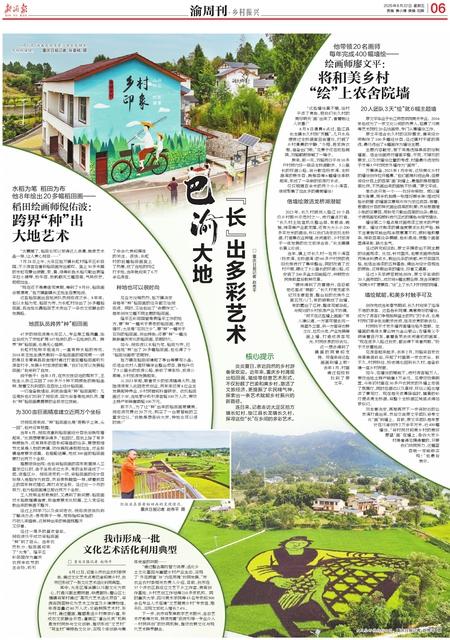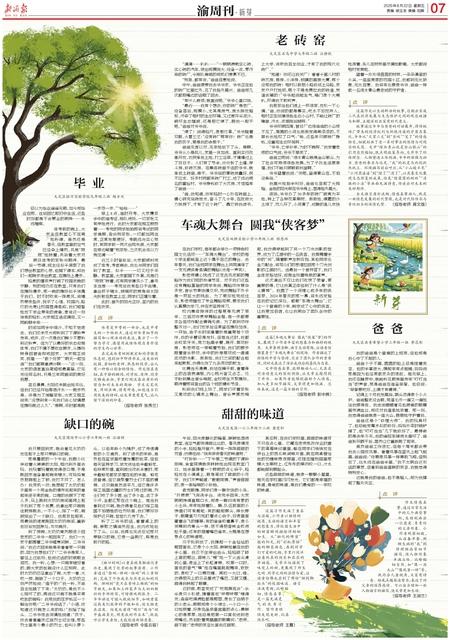A8:渝周刊·龙水湖
□周康平(重庆)
西沱,这座长江边上可寻秦汉历史遗迹的千年古镇,那条一千多步的石梯老街,是其灵魂的存在。老街有禹王宫、张飞庙之历史遗迹,还有古盐道、吊脚楼的传统文化。然而,对西沱原居民来说,若是真正提起老街,柴市坝则是西沱人绕不开的话题。只是,随着镇城现代化的建设发展,曾经人声鼎沸的柴市坝,那个每逢赶场天人挤人的柴市坝,早被拨地而起的楼房取而代之。
不管怎么变化,历史的存在总是不可磨灭的记忆。西沱柴市坝亦然如此。它曾陪伴了西沱人一代又一代的繁衍生息。为什么这样说,这得从西沱古镇的地势说起。西沱古镇是一条沿陡峭山坡而建的绵长老街,层层叠叠的房屋从山顶独门嘴延伸至长江边。狭长的老街,被老街的人称之为正街。有正街也就有背街,只是背街不是街,是山坡上的一条曲里拐弯与高低不平的泥巴小路,周围稀 稀拉拉地住着一些农户人家。整条背街,只有柴市坝是块坝子,长约七八十米,宽约二十多米,靠里边是一排粗壮的桉树,靠外边是一面高高的土石坎。站在土石坎上,可看到江面的帆船点点。
听隔壁邻居七八十岁的老人家说,他们也不知道柴市坝始于何年,他们当小孩时就在柴市坝玩耍了。不能说老街有多少年,柴市坝就有多少年,但是柴市坝存在的历史,一定是千年老街的丰富注脚。在这条满是坡坡坎坎的老街,能有柴市坝这么大块平地,已是西沱古镇难得的奇迹。柴市坝所处的位置,表面看是在背街,上下只有一条泥巴小路与之相连,但是,正街有多条与背街相通的小巷子,人们穿过巷子就相当于穿越到了柴市坝。正街一侧,靠柴市坝的居家人户,他们更是方便,打开后门,就可走向柴市坝。
柴市坝这地名听上去很土,没有禹王宫、张飞庙、吊脚楼这些名字吸引人,它在西沱人的生活中,在过去相当长的岁月里,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那时,镇上的所有人烧水做饭所需的燃料,几乎全是来自柴市坝的木柴。
我对柴市坝的记忆,与我的邻居李叔叔有关,那时他在镇上仅有的一家餐馆当厨师,同时负责采购餐馆的木柴。那时,西沱古镇是七天赶一次场。街上的居民得在赶场天里,采购完一个礼拜甚至更长时间的木柴。李叔叔所在的餐馆生意兴隆,是烧木柴的大户。
一到赶场天,李叔叔与老街的许多居民一样,天刚亮就赶到了柴市坝。那里聚集着一堆又一堆的卖柴人,他们大都是穿着灰布和蓝布衣衫,头裹白色帕子,脚穿草鞋或布鞋的中年汉子,也有身体结实的大婶大妈,他们并不是以打柴为生的樵夫,只是来自山里的庄稼人。这些人一边擦着额头上的汗水,一边朝挤入柴市坝买柴的人热情吆喝。在拥挤的人群中,不少卖柴的人,能一眼发现李叔叔,然后上前拉着他的手说他们今天的木柴,晒得有多干燥,没有一块湿柴,柴劈得长短又合适,烧火煮饭,特别方便,是你们餐馆需要的最好木柴。
李叔叔是老买柴的行家,不会听卖柴人嘴上的话,他有他的验货标准:伸手拍拍捆在外面的木柴块,歪头细听其回声,然后张开双臂,对捆绑得又粗又大的木柴,用力朝上一提,便可知道这捆木柴是不是卖柴人说的那般好,从而决定这捆木柴是不是可以成为餐馆的木柴。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外地便宜的煤炭,被一艘艘驳船运到西沱江边,老街的蜂窝煤厂随之兴起,方便实慧的蜂窝煤成了老街每家每户的选择。存在了不知多少年的柴市坝只得徐徐落幕,淡出了古镇的生活舞台。感叹之余,又欣慰于胸,正如老话所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柴市坝的消失,换来的又何尝不是一个新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