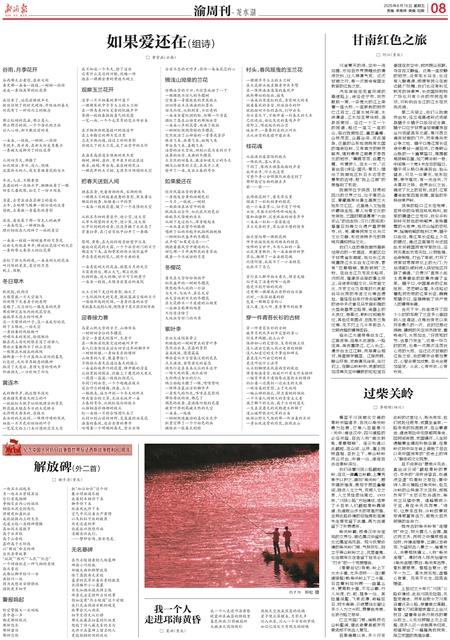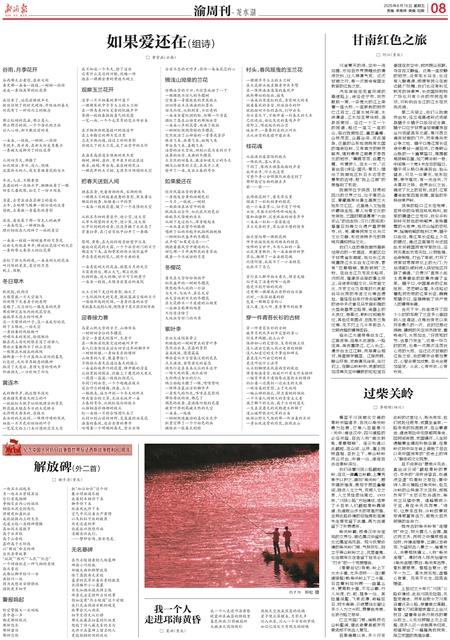
A8:渝周刊·龙水湖
□李刚明(四川)
横亘于川陕南北交通的秦岭关隘诸多,而犹以柴关岭最为险要,它是八百里秦川(关中)通往汉中、四川道路的必经关隘,自古人称“南北锁匙,秦蜀咽喉”。连云栈道以此翻越,在山间、丛林、崖上婉转盘桓、百折上下,崇山峻岭两山对出,中通一线,逶迤而去往秦岭深处。
我们沿着川陕公路翻越此岭,但见一碑矗立岭巅,上覆秀亭予以护之,碑刻“柴关岭”,题字遒劲雄浑,傲视于层峦叠嶂间,陡添人文之气,耳闻人文之息,人文灵性萦绕周边。1935年,“川陕公路”方始建成,结束了千百年人们翻越秦岭靠驿道、栈道跋山涉水的艰难历程,主持此路修建的总指挥赵祖康先生挥笔留下此墨,再为古道留下了珍贵遗存。
柴关岭巅,即是汉中与宝鸡的交界处,南边属汉中留坝,北边属宝鸡凤县。现今恢复修建的柴关岭门楼,气势恢弘,挺立于崇山峻岭之上,犹显崔嵬,也给南来北往者留下驻足必须“打卡”的一个完美理由。
《秦蜀后记》有载:岭上下大木千章,尤多漆树……在《蜀道驿程》载:柴关岭上下二十里,石齿廉利如剑锷……幽篁丛木,蒙茸数十里,不见山巅,行人与虎、豹、蛇、虺争一线。其险崖深壑、飞泉流瀑、奇峰巨石、树木森森、云遮雾绕也曾让多少人为之兴叹,赞景色秀美,也哀行路之艰辛。
伫立关隘门楼,遥眺两边山岭壑涧,惜此奇景虽感岁月更迭却不失古人复见。
自秦通蜀以来,多少行足此岭的达官仕人、贩夫走卒,他们或赴任赶考,或营生省亲,一路走来的孤苦跋涉,在山景凄迷、道途艰险中无限感同身受,因民间疾苦、家国情怀、人生际遇触景生情而吟就华章,在秦岭这块中华龙脊上造就了自古以来中国独有的“旅途上的诗人”群体和文化现象。
且不说李白“愿乘泠风去,直出浮云间”翻越秦岭的豪迈;岑参的“深林迷昏旦,栈道凌空虚”叹秦岭之艰险;蜀中诗人李化楠路过柴关岭,他见冷峻的山势虽不乏压抑,却慨然写下“水怒云愁鸟语欢,柴关立马望中宽。诸峰脚底小于豆,身在半天风雨寒。”诗句,让原本压抑、冷峻的景致变得更富有活力,感慨大自然顽强的生命力。
相传古时柴关岭有“连理树”并立,树大需几人合围,高达两丈多,两树之中横枝相连如桥,并建连理亭,立碑以志奇观,为留坝古八景之一,喻意友人、夫妻相扶情义,人称“柴关连理”。清时诗人陈庆怡曾作《柴关连理》赞曰:柴关有古橡,春秋屡更易。槎桠合复分,老干一为二。草木岂无知,盘错心有意。风来不化龙,因笃连理谊。
上世纪三十年代“川陕”公路修建成,此后川陕无险阻,天堑变通途。两年后数十万川军沿着这条公路,穿着单衣草鞋,背着大刀和简陋武器北上出川抗日,望着身后渐行渐远的蜀山故土,义无反顾踏上北上征程,很多人这一去就再未归来,却谱写出了一篇篇挽救民族、保卫家国的英雄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