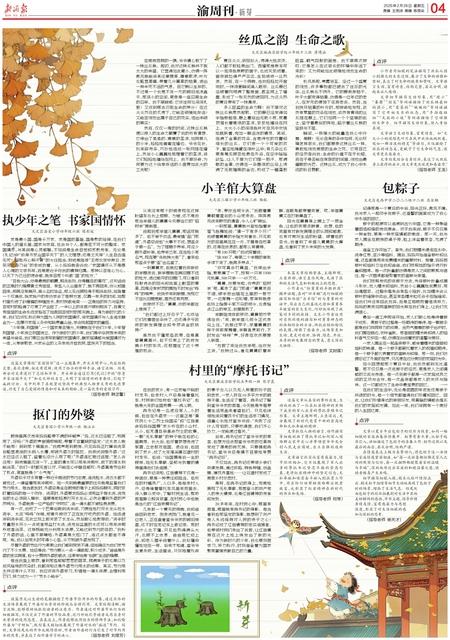A5:渝周刊·巴蜀文旅
□邹安超
有着凿痕的左右崖壁,高耸而坚硬,仿佛在述说着乡野之处的一段文明史;粗砺厚重的石缝间,深邃而神秘,似在藏匿那些不为人知的文明密码。
舞台大幕初启,左右高悬的崖壁造像与台后镜面交叠成一道时空褶皱,南宋工匠“叮当”的凿刻声穿透千年雾霭,舞剧《天下大足》通过小福被救“缘起”的场面,直抵现场观众的灵魂,慢慢展示史诗般的叙述与演绎……
以“照见自己,照见众生”为精神内核,将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雕凿史凝缩为一场关于信仰、生命与传承的史诗性展演。作为一部以“工匠肉身成史”为主线的作品,它打破了传统舞剧对宏大叙事的依赖,转而以“人间小满”的微观视角,诠释“天下大足”的终极理想。这种创作理念与传统文艺作品“从烟火处触摸神性”的哲思不谋而合,既是对历史褶皱的深情抚摸,也是对当代精神的深刻映照。
全剧分上下两场。上场以缘起、担山、采莲、烟火、传承五个篇章反映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淳朴生活,他们辛勤劳作,勇敢付出,有烟火人家的温情,有救人于危难的侠肝义胆,还有坚定不渝的信仰;下半场以小满、无常、觉悟、若水、不息,反映石刻造像的艰辛与生生不息,体现文明的传承与守护,还有舍身忘我的大爱无疆。灾难无常,一场暴风雨后,美好的家园不复存在,师父去世,亲人离别……山石无语,独活于世的小福经历了痛彻心扉的漫长煎熬,随后顿悟奋发。艳阳出来,也是小福觉悟后的初醒,前行的路很长,但不畏惧、不退缩,他要将文明的接力棒扛于肩上,坚定地一步一步向前,传承,直至生生不息……
5000年中华文明,文化璀璨,文明深厚。文化兴,则国兴。“开山化石,励志图新”八字箴言不仅是对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艰辛开凿的深度演绎,也是对中华文明瑰宝的深度挖掘,更是对中国工匠精神的现代性转译,还是讲好中国故事,颂时代华章的重度体现。
观《天下大足》,让我们一起来感知那些直抵灵魂的演绎、感受无声胜有声的心动和曼妙。
匠魂的肉身化:
从石纹到血脉
舞剧以“工匠留名”为叙事切口,将大足石刻题记中46位佚名匠人的生命史,重构为少年小福的成长史诗。小“福”即“佛”,肉身成佛,福满人间。舞台上的《父母恩重经变相》双人舞,以母子相拥的肢体缠绕,复现宝顶山大佛湾第15号龛“推干就湿”“哺乳养育”等石刻场景;《牧牛图》群舞则以竹笛与牛铃的节奏呼应,将田园哲思转化为牧童与耕牛嬉戏的野趣张力。这种“以舞释像”的手法,恰如编导刘翠所言:“让冰冷的石头开口说话,让工匠的血肉重新在舞蹈中生长。”
石刻群像的肉身转世,剧中人物皆脱胎于大足石刻的题记与造像。
媚态观音的双重人格,孟庆旸分饰的老板娘与媚态观音,前者泼辣市井,后者庄严悲悯,呼应北山第125龛“菩萨低眉处,尽是众生相”的世俗化特征;养鸡女的舞蹈人类学,双人舞段提炼自宝顶山第20号龛“养鸡女”造像,编导以川渝“矮桩步”和“扭腰摆胯”动作,还原南宋巴蜀女性的生存智慧;工匠群像的阶层切分,师父(文氏家族代表)、秀才(书丹匠人)、老铁(粗坯工)构成南宋手工业者的阶层图谱,暗合《大足县志》中“百工竞巧”的记载……
剧中匠人群像的塑造,恰是“伟大缘于平凡”的哲思与运用。师父的尺规丈量、老铁匠的粗坯塑型、秀才书丹题刻等等,每一段舞蹈皆是血肉与石壁的对话……
主演张翰的6分钟独舞堪称全剧美学枢纽。其动作设计融合川江纤夫的弓腰踏地、铁匠锻打的肌肉震颤与喘息,演绎出“诗性的痛感”与坚韧;还有凿石工匠的挥锤韵律,形成“力与美的多重变奏”。当他的脊背在顶光下起伏如崖壁纹路,汗水飞溅成星光的刹那,舞蹈已超越对劳动场景的摹写,身体语言的意象生成,升华为“肉身成史”的悲壮仪式。这种将身体作为雕刻工具的美学实验,与众多艺术家塑造的“泥土烙印”扶贫叙事形成精神共鸣——二者皆以肉身为尺,丈量历史与现实的沟壑,融精神于血脉之中。
编导大胆打破宗教艺术的崇高性,让媚态观音与沽酒女共舞、牧牛图与养鸡女并置。孟庆旸饰演的媚态观音,以水袖的弧光勾勒出大足石刻中观音造像中“东方维纳斯”的曲线;而刀妹的泼辣踏步,则源自宝顶山第20号地狱变相龛“养鸡女”的市井生机。这种“佛堂与酒肆同框”的舞台调度,暗合大足石刻“三教合一”的文化特质,其民族化、世俗化、生活化的演绎,解构出神性的从佛龛到市井的空间折叠。
匠魂的史诗化:
个体叙事与集体记忆的辩证
少年小福从战乱流民到石刻传人的成长弧线,构成全剧的情感脊柱。小福一系列经历,如逃亡与被救、收养与关爱、生与死的面临,都是群体与个体之间感情的互动,情绪的交流。当他匍匐在地摹拓师父足印时,舞台地面投影出北山第136号转轮经藏窟的千佛纹样——个体足迹与集体信仰在此重叠。这种“以足印叩问历史”的设计,皆是平凡者用生命丈量文明的有力佐证。
剧中工匠角色的肢体语言,暗藏南宋川渝的技艺密码:师父丈量崖壁的“规尺舞步”,源自《营造法式》的几何美学;秀才书丹题刻的“悬腕之姿”,化用书法中的飞白笔意;而老铁匠锻打粗坯的“金石节奏”,则脱胎于大足龙水五金的锻造韵律。这些动作不仅是技艺的展演,更是“工匠基因库”的活态传承,有群体的智慧,是集体和团结的产物。恰如编导张雅琦所言:“每个舞步都是刻在川渝人DNA里的文化记忆。”
“十大明王”舞段以雷霆之势再现宝顶山第22号龛的天灾意象。舞者们以断裂的肢体语言模拟山崩地裂,大批匠人在狂风暴雨来临时勒绳索爬山崖保护石刻,这一场面,悲壮而热烈,其同心同德、团结协作而勇往直前,痛苦又欣慰,凄凉也温暖……小福在这样的环境中,吞噬着生与死的痛,消化着舍与得的爱,让他的情感世界得以洗礼和升华。
“无常”便是“常”,一切都在生与灭变化之中,经历过生离死别之后,总会重生和涅槃,于是乡亲们在《父母恩重经变相》的乐声中重构家园,而小福,也在新生之后重振再出发,决定以山为册,化刃为笔,用余生刻石留名,令文明璀璨发光。这种“毁灭—重生”的叙事结构,暗合大足石刻“慈悲渡劫”的宗教哲学,更赋予传统舞剧罕见的史诗气质。当镜面折射出当代汶川、玉树地震的救援影像时,历史创伤与现实际遇完成超时空对话,展示出艺术重现与疗愈的无穷魅力。
技术的赋魅:
新媒体语汇下的文化遗产活化
舞台中央的巨型镜面装置,既是宝顶佛湾的崖壁隐喻,也是连通古今的时空魔方。当工匠凿刻的剪影投射其上,石刻纹路如基因链般螺旋生长;当观众的面容与佛像重叠,镜面瞬间化作“数字敦煌”的交互界面。这种“虚实嵌套”的视觉修辞,亦幻亦真,令人遐想无边……
铁凿击石的清脆高频、川江号子的低沉共鸣、竹笛颤音的田园诗意,在立体声场中交织成“声音的崖壁”。特别在《牧牛图》舞段,牛铃的方位移动模拟石刻的空间纵深感,使观众产生“耳游石窟”的沉浸体验。这种声效设计,与传统音乐中的“水声疗愈灵魂”形成通感呼应。
服装设计堪称“行走的非遗博物馆”:工匠的麻布短褐植入大足竹编纹样,沽酒女的襦裙提取蜀绣蝴蝶元素,而媚态观音的纱衣则印染北山观音的璎珞图谱。更精妙处在于材质选择——采用土生土长的国家级非遗重庆荣昌夏布与镜面涂层的混搭,既呼应石刻的粗砺感,又暗喻传统工艺的现代转型。这种“古今材质的对话”,恰是非遗文化符号世俗、生活的巧妙结合与运用。
精神的拓印:
从地域叙事到文明对话的升维
“开山化石”的重庆魂:地域文化的超克之力
剧中反复出现的“开山化石,励志图新”八字箴言,不仅是工匠精神的注脚,更暗含重庆山城文化的生存哲学。当少年小福在镜面星空中接过师父的凿刀,舞台后方投影出当代重庆的轻轨穿楼、跨江大桥等奇观——古代工匠劈山凿石的魄力,与现代重庆“向立体要空间”的智慧形成精神接力。这种叙事策略,注入重庆地域灵魂与文明基因,感受舞剧层次与立体空间的多维变换。
工匠精神的全球语汇:从大足到人类石窟史诗
通过对比敦煌飞天的“仙气”与大足石刻的“地气”,舞剧揭示中国石窟艺术的南北分野:前者追求彼岸超脱,后者执着现世圆满。当《媚态观音》舞段糅合印度古典舞的“三道弯”(暗示佛教从印度传入)与川剧旦角(本土化)手法,大足石刻作为“石窟艺术汉化终点”的文化价值得以彰显。这种“文明的对话性”,为舞剧注入超越地域的普世意义。
文化遗产活化的“大足范式”:从舞台到文旅生态
舞剧火热演绎,大足文化民俗意象的符号也随之升级传扬。剧终时无数盏孔明灯升空,鲤鱼灯舞表演,既复现2025年央视春晚的视觉奇观,又暗合宝顶山“燃灯祈福”“福满人间”的千年传统;也提示舞剧主题“人间小满,天下大足”。
舞剧以重庆作为巡演首站,接下来的全国各地演出中,力求将“唐宋风华装进文创快闪店”的文化输出策略,开创“展演融合”新模式。巡演至哪里,哪座城市同步举办大足石刻拓片展、非遗工作坊,还有石雕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雕刻技艺,同样是动与静,现代与远古的交融,让观众开启“舞剧文创盲盒”。这种将崖壁造像转化为可穿戴、可体验的文化消费品的策略,正是“让历史住进日常生活”的消费理念。当观众佩戴印有“媚态观音”的丝巾走进剧场,艺术与生活的边界已然消融,神与佛就仿佛在身边,转瞬之间又仿佛成自身的超脱感和自在感莫不就是“人间小满”。
结语:
在凿刻声中照见文明基因
当尾声的镜面星河缓缓暗去,耳畔仍回响着千年凿刻声。这声音不仅是工匠与石壁的对话,更是文明基因的代际传递。《天下大足》以其独创的“舞蹈人类学”视角,将大足石刻从地理坐标升华为精神图腾——在这里,崖壁是凝固的舞蹈,足尖是流动的雕刻,而每个观众的面容,都成为历史长河中的一尊无名造像。
“真正的文化遗产,不在博物馆的玻璃柜里,而在每个平凡生命的血脉回响中。”这部舞剧以足尖为凿,劈开的不仅是舞台的第四堵墙,更凿通了古今文明的精神隧道。此刻的舞台,已成为一座流动的现代佛龛,而我们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凿刻属于这个时代的“天下大足”。当我们在掌声中离席,带走的不是一场视角盛宴,而是一把重新打量自身文化基因的钥匙——这或许正是《天下大足》留给这个时代、留给当今每个人最珍贵的拓印。
(作者简介:邹安超,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大足区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大足区作协副主席,出版文集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