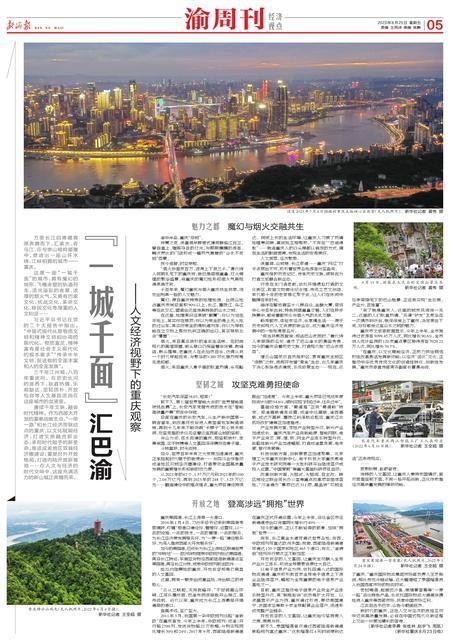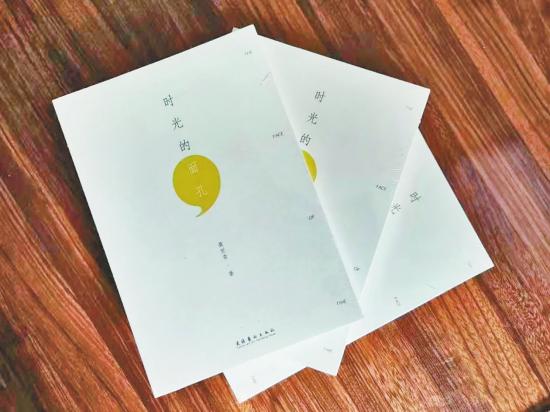A8:龙水湖/读书
□红线女
诗之于诗人是心灵之音的发声,诗人赖以发声的心灵感应,无不来自诗人生存其中的客观世界在内心世界的反观下、由感悟发酵的形而上的意识形态的情感抒发。不同的诗人因各自不同的成长背景和不同的人生经历与感悟,其抒情范畴或落脚点千差万别,着力点更是大相径庭。正如余秋雨所说“我曾把‘开掘人生况味’作为自己艺术理念的一个重点”一样,诗人聂世奇(笔名大可)也有自己的抒情方向和内容,其第二本诗集的作品尤为注重人生况味的挖掘和提升,同时也十分注重设喻的社会性或多旨性。正是有了自己的抒写目标和艺术追求,诗人在近期的创作中就多了刻意而为的努力,有意识地寻求社会、人生的独特体验,极力培养自己对社会、人生况味的敏感性,并从中找到适合自己且更能抒写自我感悟的艺术策略和写作方法,为自己的人生履历镌刻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借以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生活或人间世相。
其实,诗歌流派、题材的人为划分本身是毫无意义的,而抒写手法或艺术风格的定义同样缺乏一定的科学性。但诗人在实际创作中对抒写对象和抒怀方式及抒情策略还是有所侧重和选择的,所以,诗人聂世奇偏重人生况味的抒发当在情理之中。
当代诗歌人生况味的抒写,或浓或淡,或轻或重,或明或隐,实际上,这也潜移默化着诗歌的阅读效果。
“今年,许多的脸/被放在一起,流行/变成一本杂志的面孔/一期,一期,再一期/叠加的面孔/在月份的夹缝里堆满希望/你只需用日子的棱角/一捅,就知道/会有许多季节的虫子/从一月到十二月/不断地飞出/遮挡那脸/成了一个大大的面孔”。不知道他是源于什么写出了这首《面孔》,把许多脸放在一起,加上各种表情,就成了各种面孔,各种假面,各种面具。这里,其体现出来的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诗性之光。诗人对“面孔”一词就有着多旨性的设置,而更多的则是赋予了“面孔”的社会性,“面孔”在诗中直接呈现的已然是一种形而上的精神的诗性叙事。作为一种想象,“面孔”除了自身的自然属性,其连带的成分更加突出;作为一个意象,“面孔”在诗中的特指性同样显而易见。诗人感叹社会物象与世相的某种欺骗性和随波逐流的世俗性,从而致使千篇一律的东西往往形成一种社会潮流,成为一种风向。而某些风向竟然可以迅速深入社会的各个领域、各种层面,政治、文化,文学、文艺,甚至行政管理模式,甚至城市建设及市政设施等,不一而足。君不见,一首诗歌或其他文体作品的成功,接踵而至的就是铺天盖地的这种面孔的诗歌或其他文体作品;一个地方的公园建设有了自己独特的设计理念和元素,其他城市很快就复制无数相同面孔的公园;一个地区搞了一种什么文化节,这样面孔的文化节就在全国蔓延;各种场合呈现的事物就汇集成千人一面的社会现象,“一期,一期,再一期/叠加的面孔”“流行/变成一本杂志的面孔”。诗人对社会、人生况味的感悟,比之直抒胸臆的精神诉求就获得了一种与众不同的体验与表达。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的一天或每天,诗人自有自己的认识和定义。
在《一天,每天》里,经诗人独特的视角观照,“一天,每天”已然具备了一种新的语义,继而展现为一种周而复始的人生。诗人在“一天”的持续演进中,深刻地感受到时间“每天”都在叠加为苍茫的光阴,这种光阴的往返回复形成类似一成不变的日子,人们在这种无法回避的生存体验中,有着各自不同的感悟和千差万别的认知与情感定位,个中况味定然迥异。“往左向右,坚硬地生存/往右向左,紧密地忙碌”,这是一种个体生存常态,也是人们生活的共生性的普遍规律。对于人类,多少有些无奈的这种生存状态,在诗人的笔下却更多的是人类生存现象的必然性。
“我说不出自己来时的方向”的《那匹马》,以及“在细雨中不断地漂白,变旧”的《巷子》等意象的设置与表意,都恰如其分地陈述出一种人们的生存状态,而这期间的人们却又“无法分辨具体的年代和月份”(《巷子》),这样的生存境况,茫然中更添了几许怅然。人的生存现状虽然十分艰难,但意志仍然万分顽强,其坚韧不拔的精神将永远照亮前行的路,“赶路的千足虫,多像落难的人类”,“横穿多条崎岖的山路/找回自己的疼痛和坚硬”(《赶路的千足虫》)。人世间有阴晴圆缺、风霜雨雪,更有春光明媚、百花盛开,对明天的向往、对幸福的追求同样是人们的生活主题,“带着特产和满篮子的花朵/在温暖的阳光下/繁茂盛开”(《因为你,我才如此青春》)。而同时,团结、友情更是人类克服时艰、攻坚克难的力量源泉和精神支柱,当2020年那场新冠肺炎疫情袭来,中华大地万众一心,共赴国难。“让天使扇动的翅膀,带过去/那是圣洁的祈祷,更是大爱的颜色”“天津,武汉。两座城/一千二百公里。一封决心书的长度/我们,在上面行走”(《一封决心书》)。
诗人在感叹世事的艰辛时,仍热情颂扬人们为幸福生活奋斗做出的不懈努力。
诗写至此,人类社会的普遍性规律中的无奈得到了一次强有力的指证,与此同时也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化解。在这里,诗人的诗歌创作获得了积极向上的写作态势。
多年诗歌创作的历练,诗人聂世奇的诗写语言十分干净、明朗且富意蕴和诗韵,彰显出言简意赅的诗意表达力。我喜欢他这样的表达,看似沉稳,却情感浓烈,暗含波涛汹涌。“一个人,一只鸟/不开口,不说话/它,在树枝上站着/不孤独,脚下就是它的家/我,在雪里站着。/不孤独。身后有人类的城市”(《湿地夕阳》)。漫天大雪停下,夕阳正西沉,一个人走在深雪中,寒气从脚底浸入,像一只站在树梢上的鸟儿,看着这茫茫人世,感慨之心骤起。读这首诗,感觉他就是那只鸟儿,鲜花,绿树,大雪,土地,爱着的人,念着的人,都在他的心里,整个人间都在他心里生长,所以他不孤独,因为他对人世有着辽阔的爱和眷恋。
“补一些水,再补一些水/补一些希望,再补入一些/每年都在不断地补入/才有今天的那一弯泪眼/月牙泉”(《拯救》)。好一个“一弯泪眼”!好一个生动形象的意象捕捉,使没去过月牙泉的人深深地陷入其中了。那么爱,那么悲悯的情怀,一下子就扑到读者面前,仿佛必须去看看那只眼睛,看看它晶莹欲滴的眼泪和欲说还休的眼神。“补入一些,再补入一些/而干渴/从沙漠里,随时都可能爬出来/在瘦弱的月牙上/再咬上一口”(《拯救》)。看吧,瘦弱的月牙儿,被漫天的黄沙包裹,黄沙随时可以铺天盖地,把月牙泉一起埋葬。诗人不说埋葬,也不说铺天盖地,而说“咬”。一个小小的“咬”字,衔接了“那一弯泪眼”,更是衔接了诗人对月牙泉的喜爱,彰显了诗人柔情满怀的诗心,和对变化万千的大自然有着悲天悯人的情怀。我是真喜欢他这样的表达,干净,克制,明快而深情。
“那把陈旧的竹椅/承载了时光的厚度/仰坐在上面,一片树叶/飘落下来,在你的身上/纹理清晰/每年,每月,每日/你都在巷子的深处坐一坐/深信只要把时光扯宽些/身下的竹椅,有一天就会发芽/在生命的另一面,重新新鲜起来”(《时光》)。这首诗,很短,意象竹椅也非常普通,但就是这样简单平凡的小事物,诗人却可以提炼出精致深刻的诗意来。一句“把时光扯宽些”,一句“身下的竹椅,有一天就会发芽”,一句“生命的另一面,重新新鲜起来”,点点递进,滴滴深入,把生活的琐碎和生命的隐忍与豁达,表达得淋漓尽致。
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都在庸长平淡之中,就像坐旧竹椅。
鲜花,掌声,霓虹,总是在虚妄的镜像里。
我们得静下心来,拿出坐旧竹椅、坐冷板凳的决心,热爱自己,磨砺自己,让自己变得宽厚,变得强大,变得纯粹。
“没有出口,只能翻墙而过/很轻便地/暂停在一个角度里/爱,有时会在呼喊中浮现/我知道,你不会让爱情再一次押入当铺/绿叶,花朵,长满枝头。/时间放慢了脚步。星空下/你打开封闭已久的身体,让潮水汹涌/春天的那个眼神,打量着从远处吹来的暖风/我们都卷了进去”(《春潮》)。我把这首诗读成了爱情诗,而且是一次停止了的爱情,这份爱翻墙而入,又翻墙而走,留下爱和想念在回忆的深处。我读到了痛与不舍,读到了强烈的眷念,正如“爱,有时会在呼喊中浮现”,这是痛苦的呼喊,是忍不住的呼喊,是只有自己听得见的呼喊。
步入中年之后,爱情大多数都变成了亲情。但敏感细腻的诗人的心,总是会在繁忙、芜杂、无趣、毫无生机的生活中,一次又一次在诗歌里去虚构属于自己的爱情。这样的虚构是有意义的,可以让我们活得丰满一些、活得有趣一点。
“几年来,一直没有见到你/院内的橘子树年年开花,年年结果/想我,就到橘子的内部来找我/一瓣一瓣的思念,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酸甜杂陈,炽烈搭肩/过来吧。到时月光会站在你的身后/在第一时间/把黑夜装进白天/用第三人称/把白天引进黑夜”(《做客》)。好热烈的爱和思念!如果爱情来了,我们唯愿白天永远不要来,我们只要黑夜就可以了。
“你承认,你的梦乡里收藏了太多的她/每当黄昏倾斜到水底/黑夜出现在枕边/她的影子/就是夜里生长的一株羸弱的植物/默默生长,从不作声。/多年来/你学会用思念去浇灌,用伤口去呼吸/游走在夜的边沿。/可是,从夜空出发的雪/却从未抵达过她居住的城市/有一天。你想。/给黑夜开个窗口/她就会看到你梦的表情”(《给黑夜开个窗口》)。还是这样的爱,永远像幽灵一样,游荡在黑夜里,游荡在思念的另一面,游荡在无尽的梦里。这样的爱情,苦涩,像锯木面;甜蜜,像藏在衣袖里的小蜜蜂;疼痛,像左右拉动的锯子;绝望,像永远不会流动的死水。读着,读着,我们是一定可以得到共鸣的。
无论是生活况味,社会形态,行吟抒怀,还是爱的呢喃,聂世奇的这本诗集里,冷静地,多旨意地,真诚地,多向度地诗意表达的句子都很多,我就不一一去拣选了,有心的读者自会付出自己阅读的真心,去走进和感知诗人的内心世界。一旦你真的进入他的诗歌世界,你就会看见一个温柔、敦厚、不乏浪漫的男人,笑意盈盈地向你走来。你也就会喜欢上他的诗,或者爱上他诗里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