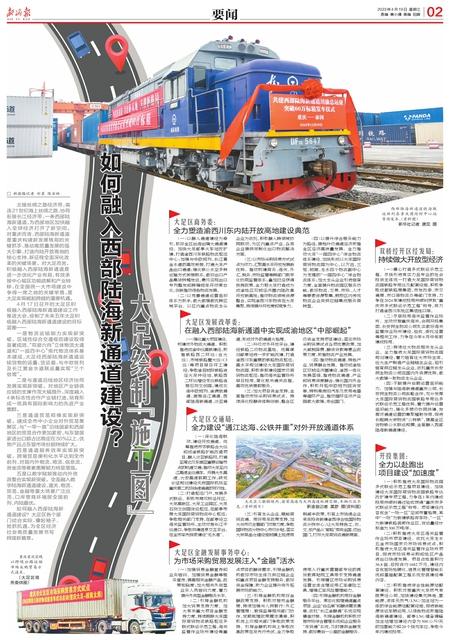A3:天下大足
近年来,千年造像常常“走”下崖壁,“活”在大众的生活中,这与大足石刻得到很好保护和宣传密不可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首任馆长郭相颖、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黎方银、大足石刻研究院工程保护中心主任陈卉丽等一代又一代“守护人”甘于寂寞、坚守在崖壁下,让“崖壁上的微笑”继续绽放下去,为大足石刻能够“发扬光大”打下了坚实基础。也正是他们的努力,上千岁的大足石刻才能“留”给下一个千年,供后世继续研究、利用。
郭相颖:择一事终一身
1974年春天,当了10年教书匠的郭相颖被调至当时的大足县文物保管所。那时大足石刻寂寂无名,大部分重庆人都不知道大足还有这样的“宝贝”。
当地人以为郭相颖是“被贬”了,把他当作“看门”的人。但是郭相颖却无比快乐。他酷爱绘画,被这些古老的精美造像所吸引,便开始一龛一窟地描画,为它们“建档”。十年间,郭相颖完成了一幅20多米长的手绘画卷,上面包括了大足石刻宝顶山和北山所有重要的石窟造像。这时,他心里已经有了一个梦想,那就是让全世界都认识大足石刻。
机会总是不期而遇。1984年,郭相颖升任大足县副县长,分管文化、旅游、城建、宗教等方面的工作。6年后,县里干部调整之际,他却请求回县文管所工作。他的理由只有一个:竭尽全力帮助大足石刻申报世界遗产。
申遗工作加快推进,而文物区环境质量是否达标,是申遗成败的关键。为此,郭相颖广泛宣传发动,让群众对环保搬迁工作予以理解和支持。18个单位、125户居民为保护文物搬迁他处,臭气熏天的水池、杂乱的摊位、污染严重的猪圈得到彻底整治。
1999年12月1日,在摩洛哥举行的第2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大足石刻迎来了申遗最重要的时刻。作为申遗代表团一员,坐在现场的郭相颖心情紧张。有国外与会专家发问,“大足石刻”和“宝顶山”是不是一个项目?眼看审议就要受阻。
急中生智的郭相颖拿出亲手绘制的长卷压缩版,来证明大足石刻的价值。最终,与会专家得出统一结论:大足石刻不仅艺术水平高,而且数量很多。以宝顶山、北山、南山、石门山、石篆山“五山”为代表的大足石刻,最终申遗成功,正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我这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把大足石刻‘搞热闹’了。”郭相颖说,从37岁与大足石刻结缘,从无水无电独自守山,到见证大足石刻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他陪伴大足石刻已半个世纪之久。对此,郭相颖总结道:“中国石窟寺保护70年,我在其中50年,可谓酸甜苦辣都尝过,十事九成无遗憾;来世若有择业时,再卧青灯崖壁前。”
黎方银:让石刻活起来
若论大足石刻现今的成就与地位,黎方银是最有资格“发言”的。
但若回到40年前,黎方银绝对想象不到大足石刻会有今日的“风光”。
40年前,文物保护理念还未普及,国家财力紧张。大足石刻的保护、研究、利用既没有专门的机构和方式方法,也没钱、没人、没技术。
2019年9月6日,《大足石刻全集》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举行。这部耗时14年、蕴含着黎方银等人在大足石刻研究、保护方面全部心血的书籍一经问世,便成了我国针对一个大型石窟群编写的第一部比较全面的考古报告集。
“两件事情一对比,说明了大足石刻的研究、保护、利用越来越成体系。”黎方银说。
保护好大足石刻,是为了让它“活下去”。那么,“走出去”,是为了让大足石刻“活起来”。
2001年,“世界遗产——中国大足石刻”大型图片展览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展出。
2011年,当地时间1月25日,“崖壁上的瑰宝:中国重庆大足石刻展”在英国威尔士国家博物馆举办。这是大足石刻首次走出国门办展。这场展览游客量超过7万人次,创下了所在展厅单项展览游客量的最高纪录。
2021年,“殊胜大足—大足石刻特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时隔20年,大足石刻再次在北京展出。
“近年来,我们做了很多关于大足石刻文化走出去的探索,包括大足石刻世界巡回展、‘四百工程’、大足石刻冠名高铁列车、参加《魅力中国城》《石窟中国》等栏目拍摄等等,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黎方银介绍,自2018年启动“大足石刻‘四百工程’主题文化旅游推广活动”以来,大足先后在重庆三峡博物馆、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天津滨海美术馆、广西柳州博物馆、四川金沙遗址博物馆、江苏苏州博物馆、深圳南山博物馆等地举办了多场大足石刻主题展览,观展人数近80万人次,不仅展览本身赢得了观众的好评,更引起了观众到大足石刻现场看一看的极大兴趣。
如何“让精美的石刻会说话”,黎方银回应,有诸多设想和计划正在逐步落地。比如,将探索完善大足石刻研究院工作机制,加大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加强与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的交流合作,着力将大足石刻研究院打造成世界知名研究院;进一步加强景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互联网+”技术运用,全方位推进智慧景区和智慧博物馆建设。
前路遥遥不足为惧,因为来路艰辛都一一扛过。黎方银担任过多个职务,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同时也是大足英才、重庆英才。在耀眼的光环之外,黎方银却偏爱仰望安然若素的石刻造像。“与其对视,回忆思索,我仍是当年那个满怀热忱的青年。”黎方银说。
陈卉丽:“半路出家”的文保专家
身材瘦小,戴着眼镜,但陈卉丽锐利的目光显示出沉稳和主见。她常说:“只有修复好文物,才能让我内心真正平静,我愿为此坚守一生。”
从针织厂车间主任到涉足技术含量极高的文物修复,陈卉丽边干边学,白天请教同事,晚上啃书本“恶补”,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多年后,陈卉丽从一位外行,“华丽转身”成为独当一面的优秀修复师。
2008年5月,国家文物局将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修复列为全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当时,千手观音造像病害已达34种,拯救“千手观音”刻不容缓。
陈卉丽清楚地记得,2008年6月12日上午,领导安排她作为大足石刻研究院现场技术负责人带领团队参与“一号工程”时,她是既激动又倍感压力。因为千手观音造像修复工程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在世界上迄今尚无可参考的案例,修复过程中出现的每一个问题,都将是世界级的难题。而历史上的多次修复,并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记载。
但是她们团队前后耗时8年,克服重重困难,通过高清摄影,将观音像分为99个区域探查、标记病害;穿着铅衣,对石像进行X光探伤;分体式脚手架的投用,开创了文物修复的先例;在石像修复中,形成多学科多部门协作的模式和案例。整个修复过程仅填写的调查表就达1032张,录入35000个数据,手绘病害图297张、病害矢量图335幅,拍摄现状照片20000余张,编制修复实施方案1066个。作为组长,陈卉丽个人独立完成了千手观音造像80只手、20件法器的修复方案编制、本体修复和修复技术报告编写。
2015年6月13日,当看到千手观音“金光再现”的一刹那,陈卉丽思绪万千,眼泪不自觉地淌落下来。
完成“千手观音”修复工程,陈卉丽在文物保护领域名声大噪。面对大足英才、重庆英才、全国“三八”红旗手、党的二十大代表等纷至沓来的荣誉,陈卉丽依然平静如初。“保护文物,就是守护我们民族和国家过去的辉煌,今天的资源,就是未来的希望。”陈卉丽说。大足石刻的75处5万余尊造像,如今已经进入高速风化期,这些宝贝的修复不是一代人的努力就能完成的。现在的每一天,他们仍然处于超负荷的工作中,当一尊造像修好的同时,又有另一尊造像亟待修复……
从守望到守护再到守责,郭相颖、黎方银、陈卉丽他们在镌刻着先人足迹的崖壁下,以青灯为伴,用一颗恒心守护,甚至花上一辈子时间也无怨无悔。
(大足区委组织部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