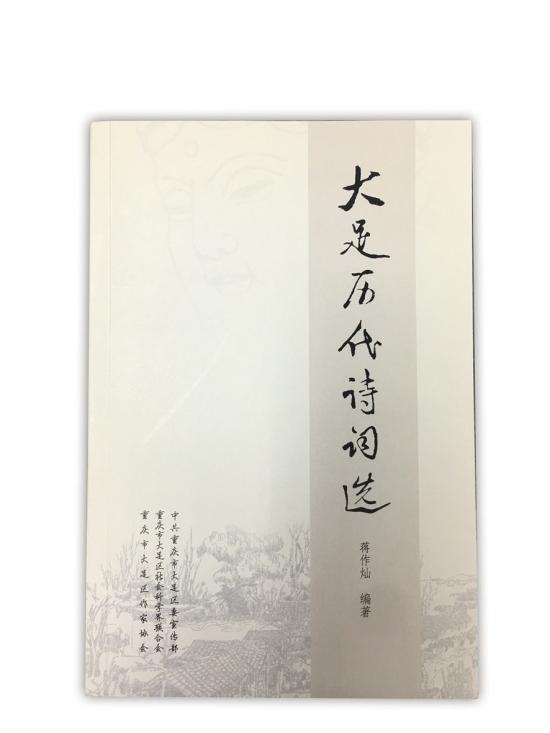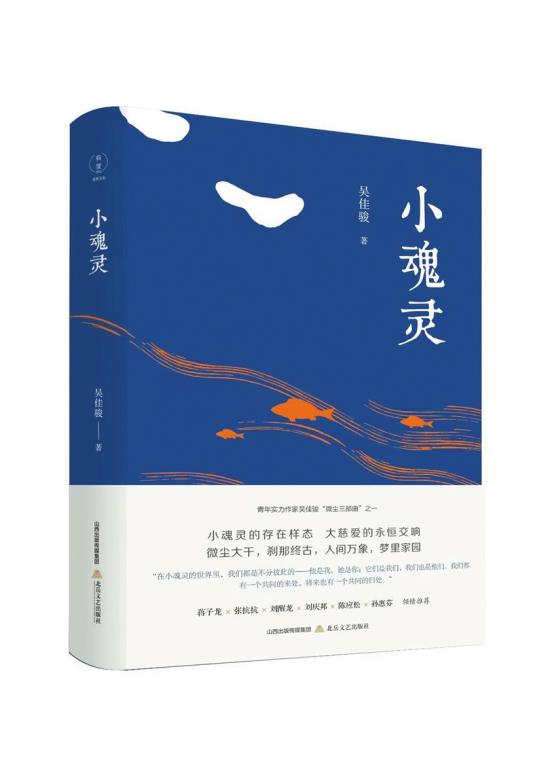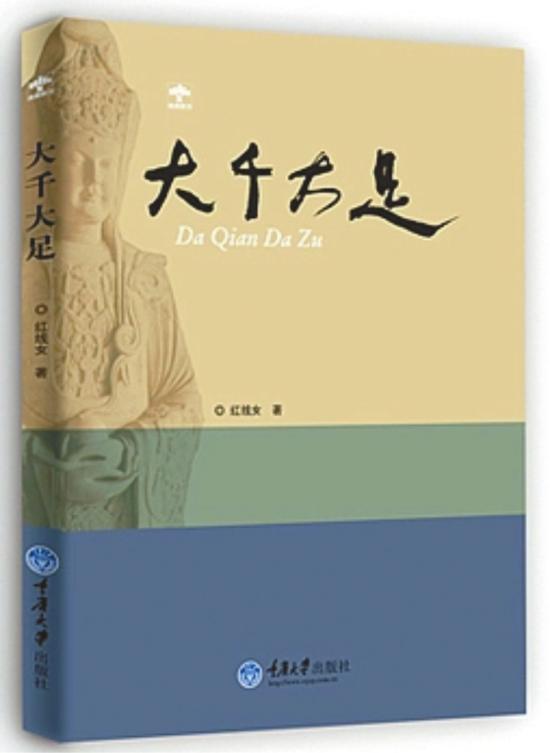A8:龙水湖/读书
□南华音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现下,我们时代的文化景观已融入我们日常生活的一呼一吸间,所以当我们在表达对本时代的生命情感体验时,文学以其特有的载体形式,给予了我们滋养,并时刻提醒着我们,返本而开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绽放了千年的璀璨与辉煌。因此本文就从文学的角度,浅谈如何在“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时代号角中,同传统文化相伴,以文学安顿心灵。
首先,我想说说何物可“安顿心灵”。《哲学的精神》(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一书中有着这样的描述:“苦海无涯回头是岸,岸在何处?这个岸至少有三个停靠的港湾:哲学、宗教和艺术”。这样看来,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作如是解,即安顿人一生肉体的无非就摇篮、木床以及棺椁,而安顿人一生心灵对应的也就三样:哲学、宗教和艺术,但在这里,我更想把其中的“艺术”一词称为“文学”。究其原因,这无非是我们所称谓的“中国艺术”,千百年来已经无意识地渗入我们的文化脊髓和文学血脉之中而不可分割了。解释完“安顿心灵”一说,接下来,我们再来厘清一下文学创作和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众所周知,传统文化的内容,有的因沿袭而“续”,有的因革新而“去”,于浩瀚历史长河中,有时有所减损,有时又有所增益。而任何一种文学创作如果不在某种传统文化中扎下根来,那么这种文学创作虽不乏行文著书者,但其实是对传统文化根基的一种偏执地背离,而且是不自觉的背离。故此我想,当下的文学创作于优秀传统文化而言,它融于文化浪潮里恣意翻滚流淌,然后在不断东风和涨潮作用下,激越起无数文学的新潮与浪花。
解释完“文化、文学、心灵”三者之间的关系后,下面就以大足区作者的三部文学作品为例,来看这些流萤般微小的文字,如何汇聚点亮和层层构筑成文学的佳作,再来看这些文学的佳作如何来源于生活,如何书写着人民,又在吟唱低语间,无声地安顿着人们的心灵。
《大足历代诗词选》,“根植巴蜀沃土,汲取棠城底蕴”。
这本由大足区作协选编的书,共选录了宋元明清、民国及当代与大足有关的古典诗词三百余首,其来源于大足石刻中的摩崖题刻、碑刻,大足县志等,参考《金石苑》《大足石刻铭文录》《大足历史文化大观》等重要书籍。漫步诗词佳苑,不管是“频年来往古昌州,览胜曾登汉相楼”“轻袍白马翩然去,念取昌州旧海棠”,还是“峥嵘宝顶迥超群,鸾啸孙登断续闻”“佛似囊锥得脱颖,地因斧凿遂扬名”,这些文字可以透过纸页,穿过时空,把内心深处一股深刻有力的生命的心跳,用文学的方式加以保存和刻录,让人在直面它时既怯懦而又感动。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由此我选取了《大足历代诗词选》中的《到家》与大家一起乐享。“一肩行李九秋归,稚子候门笑语微。藉慰故园双菊瘦,小休新种雨梅肥。”这首诗没有华丽的遣词造句,有的只是岁月平淡且静好的无忧,对归乡的渴望、对羁旅的释然、对故园的记忆、对热土的希望娓娓道来,足以一笑淡然、足以静慰人心。
进一步说,我为何会在浩瀚诗海里独独采撷这首,因为我总是相信一个朴素的真理,优秀传统文化是为人民而存在的,而文学是也为人民而存在的,文学之于人民本应如此。
倘若我们普通的民众在文学作品中得不到精神的养料、心灵的慰藉、自我的观照;倘若我们普通的民众生命情感不再有机会在文学家的作品当中得到表现、提升、洞察、品悟,那么文学也就远离了人民的生活,不再充当传统文化在浩瀚历史长河前进的扁舟角色,而是沦为单一对审美趣味的满足、以及情感宣泄的手段。此时的文学就不再作为文学,而如同阴翳般掩盖了人民生活本身应该被赋予的意义和真相,进而也就模糊了传统文化在沿袭中“续”和“去”的边界。回到诗词本身,我想这也是我之所以选择这首诗的一个重要原因。
《大千大足》,“悬知千载后,记有华章来”。
保护好研究好利用好大足石刻是大足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号工程”。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如果想要详解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的气韵余味,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大足诗人红线女所著的《大千大足》的世界。
“天大亮后/我看见她坐在石头上/面带微笑/鸡笼盖子轻轻飞起来/两只鸡宝宝伸长脖子/正啄食一条大蚯蚓/还有一只鸡宝宝/在叫/在喊/在扑腾。”《大千大足<养鸡女>》
大足石刻的出现,不仅让佛经里的“缘起性空”说起了汉语,其本身就是佛学中国化的证明,是传统文化兼容并收的变相和演化。而诗人《大千大足》的成文著书,则采撷了晚唐的月光,把石头的低语、峭壁的精魄、日子的烟火,辉映在棠城的大地上,从无到有,从开始到无限。诗人拾掇起大足石刻,在文学的世界里构造出一个属于人的感性世界,感性的日常形象也随即被灌注其中。我们透过《大千大足》看摩崖上的它们,在一行诗一行诗的点化里,心灵不再流浪,文学在本土得以安顿,同时也在传统文化的东风吹拂下,为人类自身营造出一个对真理洞察和感悟的家,一个可能会出现在远方的、被人们所期待的“家”。
“我看见笛女/戴红巾/垂长辫/柳叶入眉/眼含明月/一支玉笛横在手中/笛音袅袅/大地洞开/彩云飞舞/百鸟欢腾/它们飞过山岗,飞过悲悯,飞过永恒。”《大千大足<吹笛女>》
诗人凝神运笔,从宝顶的山巅云雾上徐徐走来,以短句的文体不疾不徐、娓娓道来,让这本书所蕴含的史料价值,活出一种超越永恒的姿态,这注定会使它比一本普通诗集的寿命要长,因为它扎根于传统文化,而长于文学的树干上,当它以俯视的视角凝视芸芸众生时,往来的人海皆震撼于它千年繁茂的文字绿叶,那一刻,心自澄明,物我两忘。
《小魂灵》,“微尘见大千,刹那见终古”。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广大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这本散文集是大足的青年作家吴佳骏“微尘三部曲”之一,正如吴佳骏在自序中这样写道:“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小魂灵,我经常在生活的周围碰见它们——我不过是在以文字的方式向它们打招呼或点头问好”,作者像是一个“心性”的探索者、观察者、记录者,小至微尘细雨,大至生死无常,他写的文字都是他心境和人格的外化。这些热气腾腾的文字仿佛让我们的灵魂置身其中,渴望着与书中那微笑平凡的生灵万物一一相逢、一一对话。
让我们来看看他是如何写故乡的池塘的:
“池塘是村庄的眼睛。有风吹,它就眨一下。若无风,它就老是睁着,望向天,好似天上会落下黄金。这只眼睛,很亮,很清澈。他会把看见的东西尽收眼底。云过,它把云的形态藏进水波;鸟过,它把鸟的影子印在水面。”《小魂灵<池塘>》
这是多么具有灵性的文字,鲜活而干净,平凡却又让人会心。文字是可以穿越时空的,当你无意间阅读到的文字,可能会让你走进作者内心的微观世界,他或许会寄生在一粒石子儿里,或许会停留在雪花的六角上,或许会遨游在深海的鱼鳍里,或许会鸣叫于夏蝉的声波中,隔空的并不是存在的距离,相遇即是合理。你依旧可以透过书页和他对话,依旧可以触摸到点滴文字里,那藏着池塘深处庸倦的眼睛,依旧可以聆听作者那可爱又坚韧的小小灵魂里,正在悄悄地给本土乡村树碑立传,也正在温柔地叩击着传统文化微掩的心扉。
再让我们看看他是如何写已生华发的父亲的:
“这些话闷在我的心里若干年了,跟屋顶上的瓦片一样,全都长满了青苔。青苔长在瓦上,就像白发长在父亲的头上。青苔和白发,都是岁月的物证。”《小魂灵<青瓦>》
作者想写一些身边的人、一些接地气的事、一些小到好像不能入文的情绪,因为那是最熟悉的人,反而一次次迟疑,挡住了以往泉水般奔涌不断的思绪,让琐碎细小的回忆在笔尖踟躇打转,翻来覆去却又迟迟无法落下文章的第一笔。他焦灼却又不自知。作者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也是一个在大足成长起来的文学青年。看他的文字,会有一种透过其内观和描摹自己的感动,或许他的文字本身,就代表了这片水土所哺育滋养起来的青年一代,以及大足文学那犹如群星璀璨般的闪耀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
我们脚下的这片热土,总是不断给予我们以无私的厚爱和物华的雅韵,让大足人民创造着独属于自己“根生土长”的优秀传统文化,也让大足人民在此基础上耕耘出“海棠独香”的特色文学。不管是本土优秀的传统文化,还是钟灵毓秀的卓尔文学,亦或是鸾翔凤集的文人雅士,这些都来源于和大足人民自身的相互成就、相互成全。对于涵养大足人文精神和气质,做靓享誉世界的文化会客厅、建强链接成渝的“两高”桥头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我们用优秀传统文化点染生命情感体验的同时,优秀传统文化和文学也在相伴而行,以文学安顿心灵,让远方有“家”可归,让未来路上无限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