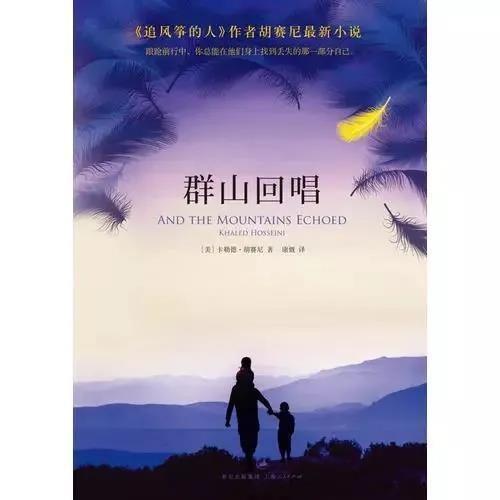A8:龙水湖/读书
□春海
1
与妈妈视频通话的最后,我照例询问起爷爷的情况。妈妈的手机镜头转为后摄,屏幕上的画面随着她的走动而来回摇晃。直到画面暗下来,我知道这是来到了爷爷的屋子。这是充满着老年人特有气息的屋子,不必仔细去用鼻子嗅闻,空气里已经充满了疾病和衰老的因子。哪怕是隔着手机屏幕,我仍能感知到它们的存在。窗帘拉着,仅有一线细细的光从接缝处钻进来,落在爷爷的床上。我看到很多熟悉的物件,比如那个插着长长吸管的康师傅牌冰红茶塑料瓶子,是为了方便爷爷躺着喝水而放在他枕边的。还有爷爷一直坚持不肯换掉的军绿色旧褥子。他的脚从被子里探出来,皮肤被高锰酸钾染上紫色和黄色,干枯细瘦却又异常肿胀,接近于青紫色的脚趾甲因为充血而鼓胀着。
妈妈固定好手机,画面稳定下来,爷爷正在画面中央安静地睡着。一天二十四小时,爷爷每天清醒的时间不超过五个小时。我其实不喜欢也不敢仔细看爷爷。我不想看到爷爷瘦得只剩下一副骨架的身体,皮肉松垮地挂在骨头上,走起路来吃力地晃。我也不想看到他睡觉时的样子,双眼紧闭,眼皮耷拉着,没有牙齿的瘪瘪嘴巴张开,露出红色的牙龈。我没办法将这个邋遢又瘦小的老人和那个瘦高的神采飞扬的爷爷联系在一起,也不愿意这样做。可是每当他睁开眼睛,灰色的浑浊眼睛看着我,咕哝着问我过得如何时,我又会乍然惊醒,为我产生这样的想法而内疚。
我尽可能地让自己接受这样的爷爷,可每当夜深人静之时,总会有飘渺轻烟一样的画面从记忆的深海里浮起。一边走路一边说个不停的小孩,身旁瘦高的中年人拉着他的小手,那平静且带着笑意的目光时刻追随着他。我时常为这一刹那的画面心悸又困惑。
这样的困惑与痛苦不停地撕扯着我,直到读了胡塞尼《群山回唱》,我才渐渐理解,我的迷茫或许是千千万万人都曾经历过的。
2
在阅读《群山回唱》之前,提及阿富汗,我的脑海里往往会立刻浮现“贫穷”“混乱”“难民”此类词汇。它与和平、稳定的中国社会完全相反,就像是与我们所在的世界完全割裂的异世界。然而正如作者所希望做到的,“拂去蒙在阿富汗普通民众面孔的尘灰,将背后灵魂的悸动展示给世人”。这片土地孕育着的人们和其他地区的人们没有任何不同,他们也只是普通的人类,有亲情、爱情、友情,有龃龉与仇恨,有亲密与爱意。
故事发生于阿富汗的一个小村庄沙德巴格。阿卜杜拉所深爱的妹妹帕丽被父亲卖到了喀布尔的富人家庭,为家庭换取到了过冬的足够钱财。从此,十岁的阿卜杜拉与三岁的妹妹帕丽经历了一场永生难以挽回的骨肉分离。
虽然故事的主线是阿卜杜拉与妹妹帕丽用尽一生来等待重逢,但胡塞尼却不止写了这一对兄妹的故事。他以这对兄妹为出发点,发散开来,描绘出很多人的人生,交织成了一幅阿富汗人的生活图卷。
纳比是帕丽的舅舅,他在喀布尔的一位富豪瓦赫达提·苏莱曼家里当管家,并对这家的女主人妮拉萌生了朦胧爱意。妮拉早年生病故而无法生育,十分渴望有一个孩子,因此纳比牵线帮助妮拉获得了帕丽做自己的女儿。然而好景不长,苏莱曼得了中风病,就此瘫痪。妮拉本就与苏莱曼没有感情,于是带着帕丽离开喀布尔前往巴黎。纳比一个人留了下来照顾瓦赫达提,只有他能听懂苏莱曼的咕哝声代表什么,只有他能理解苏莱曼的每个眼神是什么意思。他们就这样一年一年地老去,直到有一天纳比收拾苏莱曼的画作时,才发现苏莱曼曾经专注绘画的对象全部都是他。那画作上的每个轮廓都镶嵌着苏莱曼对他的爱意。这才使他明白过来,原来从一开始苏莱曼就爱上了他。但苏莱曼始终没有向他表白心意,直到纳比四十岁时,苏莱曼请他离开自己,去组建自己的家庭。然而纳比却选择了留下。
纳比为何选择留下?也许起初仅仅是因为苏莱曼需要他。而后来他的心境逐渐改变。在纳比看来,他已经拥有了人们在婚姻中追求的东西。一个舒适的、始终接纳他、爱他、需要他的家,还有一位与他互相理解的伴侣。他们一同经历了喀布尔的平静无波与战火纷飞,直到苏莱曼因病去世。在苏莱曼临死之际,纳比终于下定决心,躺在苏莱曼身边,把他干瘦的身体搂在怀里,轻轻亲吻了他干裂的双唇。
胡塞尼写纳比和苏莱曼的故事既浪漫又残酷。我曾以为死亡作为一场沉重的灾难,该是盛大而隆重的,每个人的死亡都该被特殊对待,然而看到苏莱曼的死亡,却让我突然醒悟过来。当每个人都会经历死亡时,一个人的死去正如一只鸟儿叼起小虫般,没有人会在意世界上有一只虫被鸟儿吃掉了。
一些影视剧或者文学作品中在描绘某个角色死去时,常常用环境来渲染和衬托这场死亡是一个怎样令人痛心的悲剧。比如角色死去时,天色昏暗或者电闪雷鸣,好像整个世界都在哀悼这个人的死去。然而本书中的苏莱曼却只是在一个平静的、阳光明媚的早上静悄悄地死去。同在一条街的晚起的店家很快就要开门,小男孩走在上学的路上,尘土飞扬的马路上走着一条懒洋洋的狗,黑云般的蚊子围在狗头周边盘旋着。两个小伙子合骑一辆自摩托车,后面那位跨坐在车位的货架上,一边肩膀扛着电脑显示器,另一边扛着一颗西瓜。
死亡就是这样普通的事情。胡塞尼在这里帮助读者取下了死亡的面纱。
3
年仅四岁的帕丽跟着母亲离开喀布尔来到巴黎,那些关于兄长阿卜杜拉和父亲萨布尔的记忆逐渐被淹没在了时光的洪流里。
而帕丽与养母妮拉完全是两种人。妮拉是个极具女性魅力的诗人,她向往爱情又不甘被爱情所束缚,她活得潇洒,一生放荡不羁。而帕丽却成为了一位严谨的数学家,她也不具备妮拉所拥有的美丽与魅力。这让她感受到母亲的世界与自己的世界是完全被割离开的。也许正因如此,才使得她怀疑自己的故乡并非喀布尔,自己的亲人也许另有他人。然而直到妮拉死去,也没有告诉帕丽她的亲人在哪里。
帕丽逐渐有了爱自己的丈夫和三个各具性格的孩子,对小家庭的投入使得她对自己身世的疑问逐渐消散。直到丈夫去世、孩子们也都长大了时,她才抽出时间思考自己的身世。恰好此时,借住在苏莱曼宅子里的马科斯医生读到纳比留下的信,信里记载着帕丽的童年与亲人。马科斯医生通过帕丽的社交账号联系到了她,并为她读了纳比的信。随着一字一句在耳畔响起,帕丽终于找回了那些缺失的记忆,年轻英俊的舅舅纳比,小村庄沙德巴格的生活图景,还有那双不算柔软却紧紧牵着她的手。
阿卜杜拉随着难民潮最后来到了美国落地生根。他在美国开了一家阿富汗烤肉餐厅,生活虽不算富裕,但他勤劳踏实,因此生活充实又稳定。但即使他有了自己的生活,也从未忘记自己的妹妹。他给自己唯一的女儿取名为帕丽,还为她讲他记忆中关于妹妹的故事。因此,女儿帕丽从小就知道父亲有这样一位可爱灵动的妹妹,她将另一位帕丽视作只有自己能看见的玩伴。
可惜,戏剧性的是,当妹妹帕丽终于想起哥哥,并辗转各地找到阿卜杜拉时,阿卜杜拉已罹患了老年痴呆症,认不出曾经真爱的妹妹了。但是兄妹之间的血缘羁绊并未消失,两位帕丽之间同样有着这样的羁绊。阿卜杜拉一生都在等待妹妹帕丽,她的女儿又何尝不是?当女儿帕丽终于在成年时见到那个父亲口中的妹妹时,她同样感受到了莫大的震撼,仿佛灵魂在这一霎那被填补完整了。她们叙说着彼此这些年的经历,不像姑侄,反倒如姐妹一般。
4
虽然从表面上看,故事的主角是阿卜杜拉和帕丽,但其实每个出场的角色都没有被埋没在故事主线之中。当故事里的大多数人都在尝试逃离阿富汗时,那位帮助帕丽找寻亲人的马科斯医生却恰恰相反,他离开家乡希腊四处旅行,去印度、智利、丹麦,最后来到喀布尔。在喀布尔的医院里,他看到干瘦的病人们躺在污迹斑斑的床单上,看到患病的男孩发出无声而痛苦的哀叫,他感知着来自喀布尔的苦难与绝望,最终决定留在这里。
当然,任何人做决定都并不只是因为一个原因。马科斯选择整容外科专业是因为他的妹妹萨丽娅。萨丽娅从小被狗咬伤,下半张脸只剩下骨头和一些糜烂的皮肉。因此,她几乎一生都作为别人猎奇和恐惧的事物活着,也逐渐被别人的目光塑造了人格。马科斯发现,比起内在,这个世界更关注外表。人的梦想和忧伤都被皮肤和骨骼遮蔽着。于是他选择做整形医生,他希望把外貌带来的优势平分给萨丽娅这样的人,一刀一刀地纠正这不公。在喀布尔,他为那些天生唇裂,或者因弹片和子弹造成面部损伤的人工作,完成了自己的梦想。
他的故事如果在这里结束,那么就只是再简单不过的一个治愈系文学故事。很多时候,人们只喜欢听一些有着美满结局的故事,但事实上,真实的世界里,从没有哪件事是十全十美的。
为了实现梦想,马科斯丧失了陪伴母亲的时光。当他再次回到丹麦时,他发现记忆中那个高大的母亲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瘦小的老人。而此时,他和年老的母亲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空空的洞。几十年来,母亲每日的欢笑和争吵,烦闷与疾病,正是这一长串简单的事物构成了人的一生,也构成了马科斯与母亲之间的那个永远无法弥补的洞。马科斯回到童年的家里,只感到困惑。这个家就如同一本一生只能读一次的书,他读了这本书的开头,然后就直接跳去看书的结尾,如今他才明白他再也读不懂这本书了。
5
《群山回唱》全书共九章,每个章节都开启了新的视角来叙述故事,看似零碎复杂,实则非常清晰,每一条分支最后都归到了故事的主线。然而除了故事情节给人带来的感动之外,其最出彩之处莫过于胡塞尼对人性的细腻把握。他善于用最细腻的笔触,捕捉人们埋藏在心底里的朦胧情感并将它们置于阳光之下,供所有人观看。这很残忍,但也同样引人深思。这世界没有绝对的黑白、好坏之分,每个人做下的决定也绝不能单用善恶来做评判。
正如书中的马科斯医生所感受到的那样,老去的母亲与曾经的母亲被割裂开来,我感受着现在的爷爷也与曾经的爷爷割裂开来,但无论是哪个爷爷,他们都是我的爷爷。我们之间的血缘的联结永远无法被磨灭,我始终会为了爷爷受到的苦难而悲伤心痛。
《群山回唱》为我带来的不仅仅是对人性的更深层理解,更是对自己的救赎与解脱。那些曾令自己都觉得不堪的内心想法,也不过是万千人群中每个人都会有的心声。